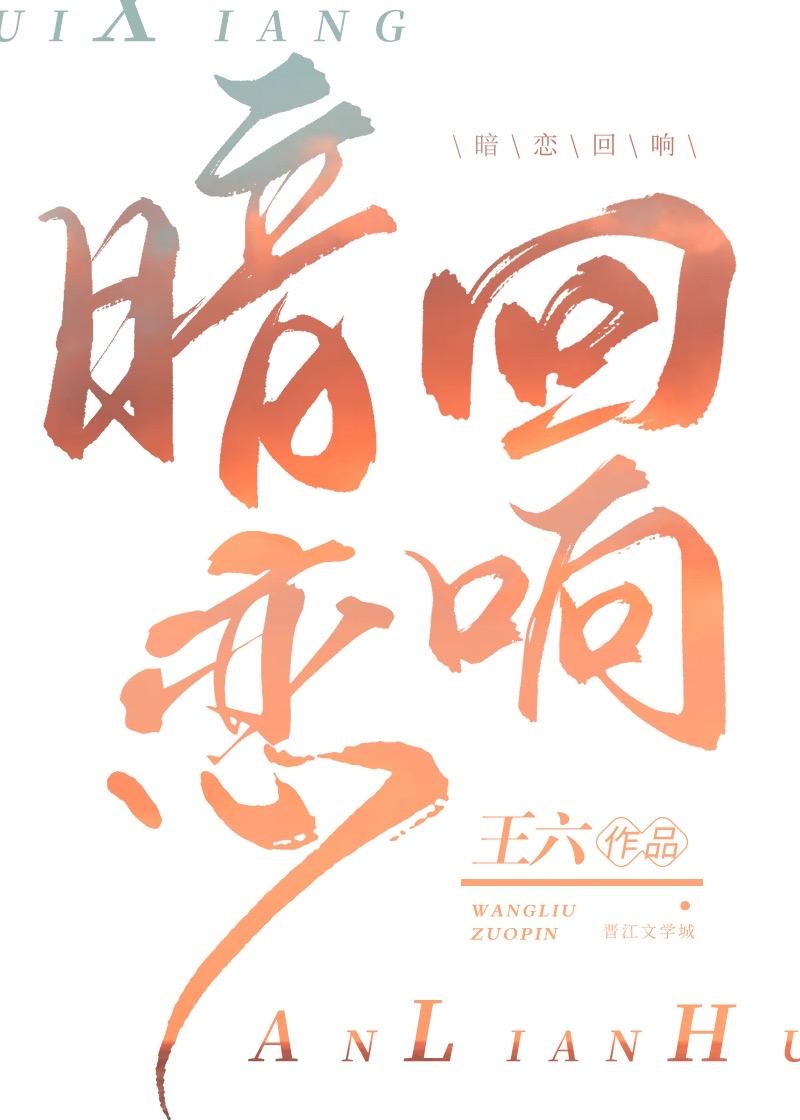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竹坞巷的葛春妮 > 第八十一章 要横横在外面(第2页)
第八十一章 要横横在外面(第2页)
她将“小姐”两个字咬得特别狠,都能看到两个带血的牙印了。
……
葛夏妮踉踉跄跄地走在自家修的柏油路上,她都知道自己是怎样从小卖铺逃出来的。
这条路刚修时是那样的可脚,走在上面踏实,温暖,如果却被时间和冬天给磨得硬梆梆的,有些丑陋不堪。
一股钻心的疼痛从脚下往上爬行,穿过她的脚底板、腿肚子、温暖的子宫、她小心眼却并不十恶不赦的心胸、她尖酸刻薄却天生喜感的大脑,然后在眼睛中定格,凝结成珠,一滴滴向下滚落。
她从没有这么疼痛过。
她像个行尸走肉般回到葛家大院,上了二楼,进入自己的房间,悄无声息地躺到床上,用被子将自己埋藏。
吴军从上海出差回来报账时,曾和财务说他在上海被小偷割包了,丢了八百块钱。
那道口子她看过,是真真切切的刀片划破的……这么看来刀口也能造假,却真真实实地划在了她的心尖上。
被子可以阻挡哭声,却消除不掉她心头的愤恨和悲伤,她把它裹得更紧了,
恨不得闷死自己算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一把将被子掀开了。
“起来。”葛春妮站在床边说,一脸的肃杀。
她一把将被了夺过来又蒙住了头。
春妮又把被子给掀开了。
“葛春妮你要死啊——”葛夏妮像头受伤的母兽,坐起来冲她大吼,“信不信我大耳光扇你?!”
“你就会窝里横,谁打你脸了,我们陪你打回去!”春妮不由分说将她从床上拽了起来
葛夏妮愣愣地看着她,突然明白了什么,拿手使劲抹了把脸上的泪,和她一起下了楼。
楼下,大姐冬妮和弟弟似锦已经等在了院子里。
读初三的葛似锦,身高已经一米七八了,长期打球锻炼,他结实的像个铁塔。
“走——”冬妮轻声说,声音不高,但很重。
葛家姐弟一字排开横着出了大门,朝“昭夏小卖铺”走去。冬妮像个带兵的将军,一脸的凝重;春妮像像个军师,边走边将心中的作战计划讲给两个姐姐和弟弟听。
远远地,他们看到吴军已经等在了小卖铺的门口,脑袋耷拉着,像个罪犯。
出门前,冬妮已给吴军打了电话,简略讲了一下安排部署,要他出来配合。
葛夏妮的眼睛狠狠地在他身上剁着,恨不得剜下来一坨肉。爱有多深,恨就有多切。凡是被狐狸精碰过的地方,她都想拿伏尔马林给他使劲刷洗个千百遍。
冬妮冷静的像块冰疙瘩,拉了她一下:“别冲动,按春妮
说的做。”
夏妮只好将愤怒往肚子里使劲按了按,拿块大石头压上,才走了过去,挽住吴军走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