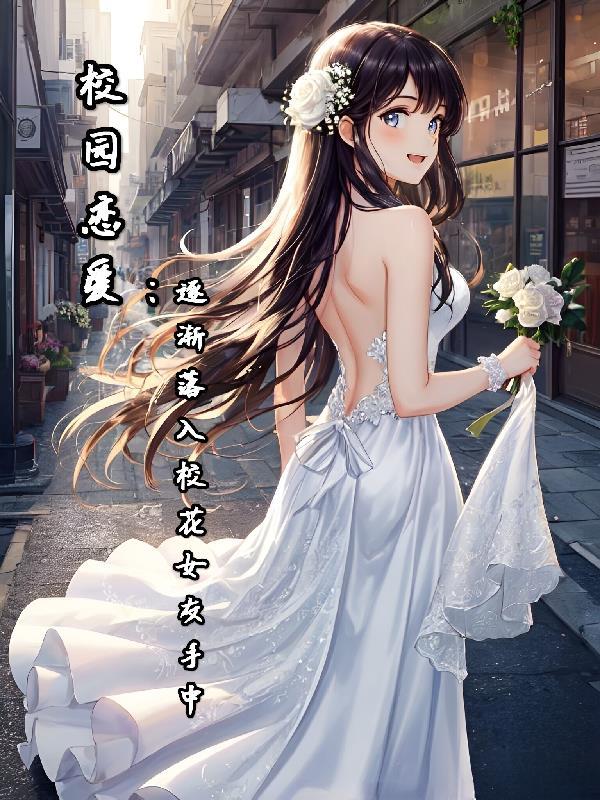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心劫 > 第105章(第1页)
第105章(第1页)
就在他们离开后不久,通往府城方向的崎岖山道上,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
陈拓浑身浴血,带着一队同样杀气腾腾的亲卫,疾驰而来,脸上带着攻陷州府的狂喜和急切,显然是想第一时间与运筹帷幄的沈今生分享胜利的果实,甚至商议下一步行动。
然而,当他冲上黑石崖顶,看到的却只有摇曳的火光、残留的血迹、空荡荡的指挥位,以及空气中尚未散尽的浓烈血腥味和药味。
“人呢?沈兄弟呢?!”
留守的亲卫队长单膝跪地,声音沉重:“禀将军,方才……方才有人行刺沈参赞,参赞为挡暗箭,牵动旧伤,伤口崩裂,血流不止,已然……已然昏迷不醒,吴大夫正在全力救治,现已移往山下伤兵营帐。”
“什么?!!”陈拓瞪圆了虎目,“刺客?!沈兄弟现在如何?!”
“刺客已被拿下,沈参赞严令单独关押,由亲卫看守,不得他人靠近审问。参赞伤势……极重,幸得沈夫人以神异针法暂时止住了血,吊住了性命,但……仍未脱离险境。”亲卫队长如实禀报。
“周通呢?!他刚才不是在这里?!”陈拓勒住躁动的战马,环视四周,厉声喝问。
“周军师在刺客被擒后曾来过,关切了几句,后来被沈参赞以稳定府城、清点缴获为由,先行支去府城协助将军了。”王管事留下的一个心腹硬着头皮补充道。
“好……好得很!”陈拓望向山下伤兵营帐区那几点微弱的灯火,又回头,望向云州府城方向那依旧火光冲天的混乱景象。
他猛地一拽缰绳,调转马头,对着亲卫吼道:“留一队人,守好这里!其余人,随老子回城!”
营帐内,灯火通明。
方才那一口逆血被强行咽下,萧宁此刻喉头腥甜翻涌,五脏六腑都像被无形的手狠狠攥住、撕扯,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针扎般的锐痛。
可她的意识却异常清明,所有的感官都集中在掌心下的搏动上。
噗通,噗通。
微弱,却顽强。
沈今生的脸在摇曳的灯火下白得像初冬的雪,左肩处厚厚的绷带被老吴头重新缠紧,她紧闭着眼,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眉头紧紧蹙着,每一次艰难的呼吸都带动胸口的微弱起伏。
“稳住了,真是神迹。”老吴头瘫坐在一旁,布满老茧的手还在微微发抖,浑浊的眼睛里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后怕,他敬畏地看着萧宁,“姑娘……不,夫人,您这针法老朽闻所未闻,参赞这条命,是您从阎王爷手里生生拽回来的。”
萧宁没有回答,她的全部心神都沉在沈今生那微弱的搏动里。
帐帘被掀开,带着寒气的夜风灌入,王管事和李铁锤端着熬好的汤药和热水进来,脸上还带着未散的惊惶。
“参赞怎么样了?”王管事声音压得极低,生怕惊扰了什么。
“暂时无性命之忧了。”老吴头抹了把汗,心有余悸,“多亏了夫人。只是这伤太重了,又崩裂失血,元气大伤,需得静养,万不能再劳心劳力。”
李铁锤将热水盆放在矮几上,看着萧宁几乎与沈今生一样惨白的脸,欲言又止:“夫人,您也……”
“我没事。”萧宁终于开口,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沈今生,“药给我。”
她接过王管事递来的药碗,试了试温度,用小勺舀起一点,小心翼翼地凑到沈今生的唇边。
昏迷中的人本能地抗拒着苦涩的味道,药汁顺着苍白的唇角滑落。
萧宁没有丝毫犹豫,含了一口温热的药汁,俯下身,用舌尖极其轻柔地撬开沈今生紧抿的唇齿,将苦涩的药液一点点哺喂进去。
帐内一片寂静,只有油灯燃烧的噼啪声和萧宁低低的、哄劝般的呓语。
老吴头再次仔细检查了沈今生的脉象和伤口情况,又给萧宁把了脉,开了调理气血的方子,嘱咐道:“参赞失血过多,元气大伤,这高热是必然的。伤口虽暂时止住血,但剜肉之创,加上之前反复撕裂,极易引发高热不退。今夜是关键,必须有人寸步不离地盯着,冷敷降温,一旦发现高热加剧或伤口有异变,立刻叫我。”
“我来守着她。”萧宁坐在木榻边,拿起一块干净的布巾,浸入王管事刚打来的冰凉山泉水中。
老吴头重重叹了口气:“你也得顾着自己些……参赞醒来若看到你这样,怕是要心疼死。我就在帐外守着,有事立刻喊我。”
“有劳您了。”萧宁微微颔首。
帐帘落下,隔绝了营地的喧嚣,只剩下油灯燃烧的细微噼啪声。
萧宁拧干冰凉的布巾,动作轻柔地敷在沈今生滚烫的额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