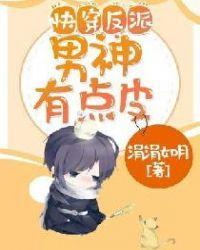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被杀死的夫君回来了 > 11吃味(第2页)
11吃味(第2页)
"娘子方才在他人面前尚且笑语嫣然,为何此刻对着为夫……却吝于展颜?”
云雀脑中仿佛“叮”地一声清响。
笑?他此刻怒极至此竟是因为自己对他人笑了?
一个荒谬至极、连她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的念头猛地窜了出来:他……该不会是在吃味吧?
不等她细想,江聿风状似无意地开口,语气却透着一股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僵硬:“你莫要多想,为夫岂会为此等小事吃味?不过是忧心娘子言行无状,与些不相干之人过从甚密,平白落人口实,惹来麻烦罢了。”
果然是吃味了!
云雀一时啼笑皆非,荒谬感冲淡了些许恐惧。她飞快回想,方才何时笑得欢了?又何时与人走得近了?
正自琢磨这“鬼夫君”的别扭心思,江聿风见她沉默不语,似乎生怕她没领会其中“深意”,竟又略显急促地轻咳一声,压低声音,几乎是咬着牙补充道:“尤其是……要懂得主仆尊卑,莫要与下人失了分寸。”
云雀简直要被他这欲盖弥彰的“解释”逗乐了,没忍住,脱口而出:“夫君是指……墨翎?”
江聿风倏然沉默。
那双一直幽深无波的眸子转瞬暗沉下去,眼底深处似有暗流汹涌翻搅。
不等云雀读懂这复杂难辨的眼神,眼角余光意外警见他的耳尖,晕开了一片淡淡的绯红。
云雀瞪大眼惊呼,“夫君!你的气血又回来了些!”
江聿风浑身一僵,旋即反应过来,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愤而松开了钳制她的手,带着一股近乎狼狈的怒意,拂袖转身。
他面向平静的湖面,静立半晌,才冷声道:“娘子若不愿这湖底的‘惊喜’大白于天下,那便谨记本分,安守妇道,切莫再起旁的心思。”
云雀在他身后暗暗瘪了瘪嘴,心头却反而定了几分。
她眼珠一转,上前一步,凑到江聿风身侧,伸手指了指湖边一块半浸在水中、缠绕着几缕青绿水草的湖石,仰起脸道:“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妾身对夫君一心一意,绝无二心。”
湖水如镜,清晰地倒映着秋日高远澄澈的碧空,岸边垂柳的枯枝,以及……岸边两道挨近的倒影。
某人的心神忽然有一瞬的恍惚。
恰在此时,一缕微风拂过湖面,细小的涟漪层层荡开,湖中的倒影随之晃动、扭曲,仿佛无声地撕开了一道时空的罅隙。
……
“嘶——”沈羡倒抽一口凉气,蹙着眉看向湖面倒影出的那个正小心翼翼为他清洗背上狰狞伤口的少女。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乌发只用一根布带随意挽着,几缕碎发垂在颊边。素净的小脸绷得紧紧的,手上动作却异常轻柔,仿佛在对待世上最易碎的珍宝。
“活该!”云雀嘴上毫不留情地骂着,手上的力道却更轻了几分,“明知自己伤没好利索,就敢偷偷溜出去。这一去一回瞎折腾,伤口不裂开才怪!”
沈羡忍着背上火辣辣的抽痛,艰难地侧过头看她,眼底带着无奈的笑意,“你这一去就是两个时辰,我怕……”
“怕我把你这个半死不活的烫手山芋给卖了?”云雀没好气地打断他。
“不,怎么会?”沈羡急声解释,“城中通缉我的画像还未撤下,你独自进城,我怎能不担心……”
“谁要你担心了。”云雀瞪他一眼,眼圈却有点红,“你乖乖待着,不让我提心吊胆,就是帮我大忙了。”
沈羡看着她明明担忧得要命却偏偏嘴硬的模样,心尖软得一塌糊涂。
他忍着痛意,从怀里摸索出一个洗得发白的小布包,献宝似的递到她眼前,“喏,给你的。”
云雀狐疑地接过,解开缠绕的布结,里面静静躺着两块小巧玲珑的玉佩。
玉质不算顶好,但雕工极为精细灵动,是两条首尾相衔、栩栩如生的锦鲤。
“双鱼佩?”云雀愣住了,声音有些发颤,“你……你这是从哪弄来的?”
沈羡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拿起其中一块,不由分说地将红绳绕过她纤细的脖颈,仔细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