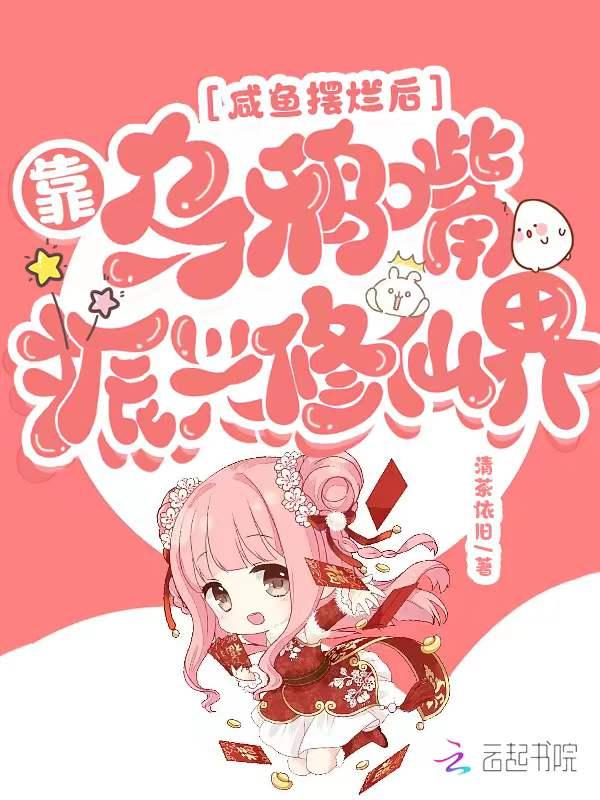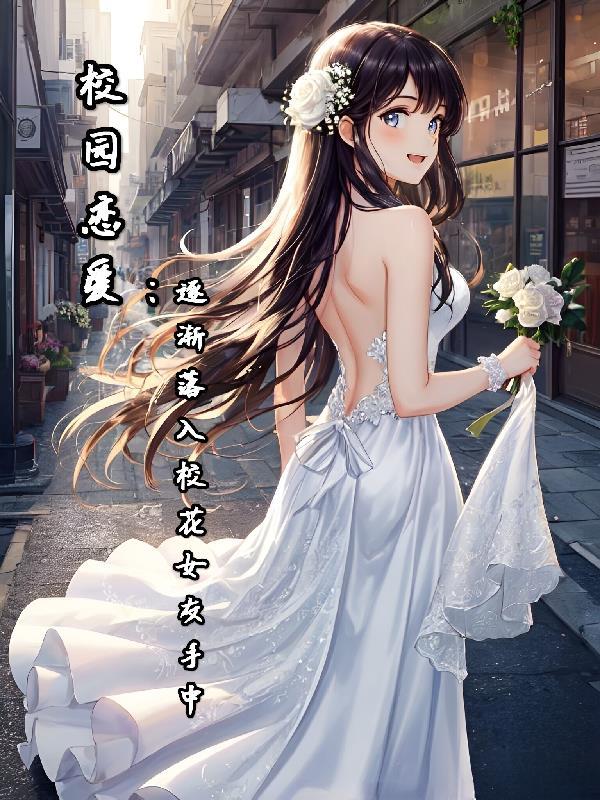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类卿 > 蝴蝶(第1页)
蝴蝶(第1页)
翌日清晨,下了一夜的雪终于哑了嗓,琅家外院的血色尽数掩埋,一片狼藉的红线、铃铛却无人打扫。
琅照守在琅昀床前,夜里撑不住睡了过去。
琅昀醒时睁眼,眼里的一切都像在浸泡在波澜不止的水里,模糊动荡。
想来还是昨日一根银针的缘故。
隐约看见身旁有个丫鬟服饰的女子,倚在床上睡着了,琅昀拍了拍那人的头,“你……”
那丫鬟抬起头,“阿兄,你醒了。”
琅昀皱眉道:“照儿?你怎么穿着丫鬟的衣服?父亲呢?母亲呢?”他说着便着急起身。
琅照扶着他道:“阿兄放心,父亲母亲都好,你慢点。”
琅昀:“他们在哪?”
琅照给琅昀倒了杯温水,琅昀接过,琅照坐在一旁将昨夜的事情一一复述。
“那我们留京是为照应父亲?”
琅照点点头。
琅昀扯开身上的棉被,“我现在就要去看看父亲如何了。”
他刚下床就撞到了床前的矮凳,矮凳被踢翻了面,琅昀也疼得收脚。
琅照跑过去扶住他,见他发狠地揉着自己的眼睛,便扯过他的手,疑惑道:“阿兄,你眼睛怎么了?看不清?”
琅昀摇了摇头,“刚睡醒,有些模糊罢了。”他拍了拍琅照的手,“我必须快些到罚罪司,你不知道,罚罪司环境阴冷,每年病死其中的人不计其数,我得去看看。”
琅照:“好,只不过,我不能同你一起。”
琅昀摇头道:“我不能留你一人在此。”
琅照解释道:“你往日出门从未带过随行女侍,跟你去,我反而可疑,不安全。”
见琅昀仍旧疑虑,琅照安慰道:“不必忧心,昨日的刺客应当已经得到了我出城的消息,不会执着于我了,我现在,只是个丫鬟。”
琅昀还是欲言又止的样子。
琅照:“阿兄,现在,我们家不能行差踏错一步了,昨日母亲同我说过,现在我们各自离散,最重要的是保重自身,其次是保全琅家,你也要记住这一点。”
无声良久后,琅昀沉声道:“照儿,你真应该把武功练好,至少可以自保,我以为从前帮你遮掩偷懒是好的,让你少受点练功的罪,却还是害了你。”
琅照扯出一抹牵强的笑,道:“让我扎马步,还不如让我死了呢。”
这是头一次,琅照笑了,琅昀却还是怅然若失的表情。
琅家没什么仆人了,琅昀便自己去马厩牵了匹棕马,临行时琅照不便现身。
琅昀的眼睛已经恢复了,回头看清了琅府的凄凉景象——门前积满了未扫的厚雪,檐下两盏熄灭的黄灯笼了无光彩。
琅昀回过头,驱马疾行。
琅照还留在春芜居,守在一个已经灭了的炭火盆前,看着黑糊糊的一片发呆。
府内三个仆人结伴竟然闯进了内院长房的住处。
“长房这回在劫难逃了,老爷下狱,夫人小姐跑路,就剩个公子挂念他老子留下来了。”
“你刚刚亲眼看他走了吧,我们不会和他撞个正着?”
“亲眼所见,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
“我们就取些小物什,不要贪心,拿好就走。”
……
门外的声音却越来越近,看来他们是直奔春芜居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