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小说网>琼珠碎又圆 > 鸣冤(第1页)
鸣冤(第1页)
使团行路缓慢,一日不过二十余里。走了五六日,才到同州地界。
赵晨撩开车帷,看道旁景色,春芳渐歇,草木愈发蓊郁成荫。看了一会儿,她恹恹道:“我以前总是不懂,那些酸腐文人为什么伤春悲秋,春光多好啊,踏青游宴还来不及呢,竟有闲工夫对花垂泪。如今才懂得,离别之苦不拘春夏秋冬的。”
冯瑗望着她,不过几日功夫,赵晨的面庞身形都清减了一些,目光却变得幽深了,气韵风致也与日俱增。正想着如何宽慰,忽听有女子悲戚的呼喊声:“冤枉啊——”
冯瑗掀开车帷,问护从在侧的章野:“章将军,发生了何事?何人在呼号?”
“末将这就去看看。”言罢,章野策马而去。
不多时,章野回来禀报道:“有个女子拦路喊冤,自称是冯翊县人,她哥哥蒙冤下狱,秋后就要问斩。”顿了顿,又道,“冲撞公主銮驾,理当重打二十,末将斗胆,恳请公主殿下念她乡野村妇,不懂礼数,一时情急,宽宥轻罚。”
“章将军可认识这位女子?”冯瑗问。章野道不识。
冯瑗这几日冷眼旁观,心知这位侍卫长行事一丝不苟,极重规矩,每日行程、安防、宿营皆照章办事,不想竟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子求情,心中不免狐疑。
赵晨问道:“她当真有冤情吗?”
冯瑗知道她素来心热,心念一动,若能让她转移注意力,少些伤感,倒也是好事,转头向章野问道:“使团可经过冯翊县?”
章野点头,“今晚就宿在冯翊。”
冯瑗的双手稍稍扣紧,父亲的名讳正是“冯翊”,似有冥冥之意牵引,冯瑗道:“劳烦章将军再去问问她,可有诉状?”
“有。”章野从怀中掏出状纸呈上。冯瑗不免又看了他一眼。
冯瑗匆匆看过诉状,眉间微蹙,赵晨急问道:“怎么样?”
“人证、物证俱备,这案子不好办。”见赵晨显出失望的神色,对章野道:“将那名女子带上。待到驿馆后,再细细盘问。”
队伍继续进发。冯瑗对赵晨阐述了这个案子:冯翊县书生何懋秀涉嫌奸杀一名青楼女子,作案手段是双手掐颈致其窒息而死。现场留有他的一把扇子,街坊证实他在案发时间内进出过被害女子的家。县令裁断,何懋秀与该女子因嫖资起纠纷,愤然行凶。
赵晨想了想,道:“听上去倒也合理,也许并无冤情。”
冯瑗道:“现在还不好说。何懋秀的妹妹在状纸中辩称,何懋秀人品端方,从不曾流连烟花地,更不会杀人,一定是被人陷害的。”
“你有什么思路吗?”
“首先要证实证物、证人证词是否确凿,还要听听何懋秀怎么说,他与被害女子是什么关系?为何在案发时间进出被害女子的家?被害女子既然是青楼女子,为何死在民宅中?第一个发现女子被害的人是谁?还要听听他的证词……”
赵晨越听越兴奋,霍然掀帷,扬声道:“章野,让队伍走快些!”
下到驿馆,赵晨来不及安置,便让人带来了那为兄喊冤的女子。冯瑗一见,即了然章野的恻隐之心。那女子自称叫何毓秀,十七八岁,眉清目秀,眉心一点朱砂痣,更添楚楚之态。她见赵晨打扮,知道是公主,跪下连连磕头,求公主为她哥哥伸冤昭雪。
冯瑗扶她起身,让她讲讲案情。
何毓秀稍稍平复激动的心情,道:“一个月前的一个夜里,官差突然闯进家里,带走了哥哥。第二天,县令大人开堂审理,我才知道他们怀疑哥哥奸污并杀害了一个女子。这是不可能的事。哥哥十五岁那年便考取了功名,后来因为父母先后亡故,才守孝在家,没有继续赴考。去年,才刚娶了嫂嫂,他们伉俪情深,从未红过脸,哥哥怎么可能和旁的女子有什么牵扯,何况还是风尘女子?这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啊。可是,有人说看到哥哥那日出入过那女子的住处,现场又寻到了哥哥的扇子,哥哥百口莫辩,已经被判处斩刑了。”
她哽咽道:“我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嫂嫂已有了身孕,我只得先瞒着她,四处奔走。我去求哥哥的朋友,他们虽然惋惜,奈何铁证如山,他们也无能为力。幸有人告诉我,公主出塞的使团会经过这里,我实在别无他法,只能冒险一试。”
“令兄可曾与什么人结怨?”冯瑗问。
何毓秀摇头,“没有,兄长是读书人,温文尔雅,平日里往来的也都是读书人,从不与人争斗。”
冯瑗又问:“令兄与被害女子是什么关系?”
何毓秀低头不安地拨弄着指甲,“我也不清楚,从未听他提起过,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报案的是谁?”
她闻言抬头,语气十分确定:“是那女子的哥哥,叫吴逵。”
“这个吴逵,是做什么营生的?”
何毓秀又摇头。
冯瑗见她并不清楚太多内情,让人先带她下去。
冯翊县令穆志成闻讯前来拜谒公主,赵晨直接问他要了何懋秀一案的卷宗。
穆县令面露难色,“此案已结,卷宗已入架阁库封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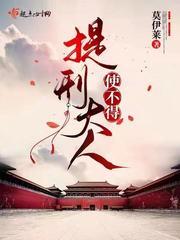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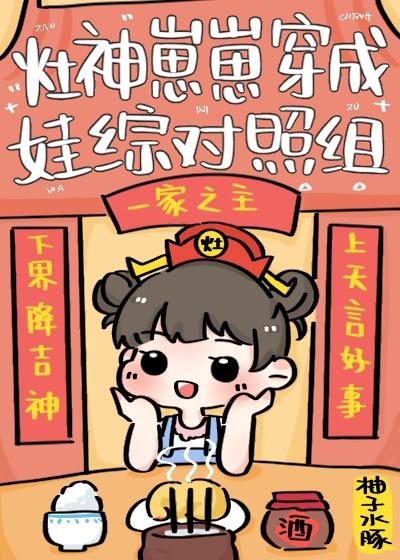
![狗血文女主摆烂了[快穿]](/img/1586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