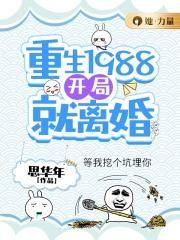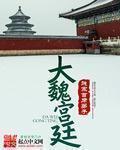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开国女帝夺权记 现实向 > 李相(第1页)
李相(第1页)
果然如唐君所料,就在当天,得到消息的李相暗中补上了所有缺额。但只要仔细一点就会发现,他所做的不过是闪转腾挪之事,在其他地方,还能查到些蛛丝马迹。若是此刻便开始严查,他便是难逃一劫。不过,李相对此毫不担心。毕竟,那个查账的能人已经被圣人送入地府。他更需要担心的,是下一步的出路。但他现在还要确定一件事,圣人是否已经对他起了疑心?
因此,他特意留了个破绽,留下了一万两白银的缺口。
圣人,会对此大做文章吗?
虽说荀忠并不抱希望,但得到了证据,也没有完全不调查的道理。于是,他就亲自带着下属去调查那些证据上的缺额,查到了其侄子在运粮官任上贪墨了一万两银子的赃款。他欣喜若狂,准备带着证据去套李相李儒的话。
李相的府邸临近宫门与长安主干道,在这寸土寸金的位置上建了一个极其奢靡的园林。大门门环用纯金打造,羊脂玉做的门槛进一步凸显了这份奢靡。而走进大门,看见的净是金丝楠木打造的楼阁,个个雕梁画柱,让每一个来者都不禁赞叹。
荀忠却只有厌恶之意,他走进宅院,努力对前来迎接的李相挤出一个笑容。
"荀将军回朝多日,可是李某人俗事缠身,未曾拜会。罪过罪过。"
李相微微拱手,算是向荀忠行礼赔罪。但荀忠径直越过这位只手遮天的权臣,在客座上落座。
李相的神情没有任何不悦,他只是默默落座。问道:"荀将军此行有何指教?"
"指教谈不上,只是有些事要来找李相确认。"
"请讲。"
"不知李相公可知晓尊兄次子偷换粮草,贪墨一万两白银。"
"哦?李某人分家之前,我那侄子还是个规矩之人。没想到离开了叔叔,竟变得如此不争气,罪过,罪过。"
李相摇了摇头,似是当真为自己的侄子惋惜。但屋子里点的瑞龙脑香已经将他出卖,清官怎么可能点得起这样昂贵的香料。
荀忠被激怒了,"是吗?不过依我之见,您那侄子若是早点与您分开,才可能不会走出违法乱纪之事。告辞。"他拂袖离开,李相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真是不知死活的年轻人。"
不过他的目的还未达到,这荀忠是动了杀心的,但圣人是否也动了杀心,尚不得而知。
他默默饮了口茶水,叫来了管家。
"叫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还没有成果。"
"废物。"
昂贵的瓷器被他扔在地上,落在管家身旁。
管家不敢躲,反倒将额头贴上碎瓷,重重地磕了个头。
"老爷恕罪,连荀忠都没找到一个吴国间谍,奴这个小小管家,实在无能为力。"
"罢了,你也暂且不必找了。若是圣人当真起了杀心,我们索性直接去投奔吴国。结果如何,明日早朝再说,你且去将那个叛徒的罪证拿来。"
"是。"
七月初三,太极宫内,气氛已有些焦灼。荀忠陈述着他的构想,要在朝中设立完整详尽的追责制度,并废除门荫制度。
闻此噩耗,许多资历尚浅的官员已有些恐惧。但李党的核心成员都还能保持冷静,一切,还在他们预料之中。
首先发难的是新任京兆尹,"据臣所知,荀将军似乎也是承蒙族中的恩荫,才在十五岁之时,就当上了万夫长。若是这门荫被废除,荀将军是否还能立于此处,还未可知。"
"勋贵亦可通过武举,当上将军,随军打仗。臣相信由李相制定的考核内容,定能为大唐筛选出合适的人才。"
李相不疾不徐地走到大殿中央,"臣相当赞赏荀将军的报国之志,只是一个远离朝堂的武将,未必擅长处理政事。更何况,这草案还未经门下省审核,将军这般越职侵官,怕是不利于朝政。臣敢问陛下,日后草拟诏令、制定政策,是否都不需要中书省?而审核诏书,也不需要门下省?臣斗胆请陛下许臣参与荀将军的改革,以确保改革的正确执行。"
"圣人御笔朱批,李相公是要质疑圣旨不成?"
"臣并非质疑圣人圣断,只是这中书省拟诏,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是千百年来的规矩。将军岂可为一己私欲,侵官夺权,越职办事?"
"李相,非常之时,应有非常之举。朕知晓卿作为三朝老臣,经验办法自然是不少。只不过爱卿侄子犯下这等恶行,为顾全爱卿名节,卿理应回避。待一切事了,朕必定给卿一个交代。"
"那臣便恭候新政成功,既然此处已容不下臣,圣人不如许臣先回去。"
"朕听闻李卿前些日子偶感风寒,自是要好好休养。朕新得一株百年灵芝,不如赐予爱卿。如今内忧外患,还需爱卿保重身体,才好为国效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