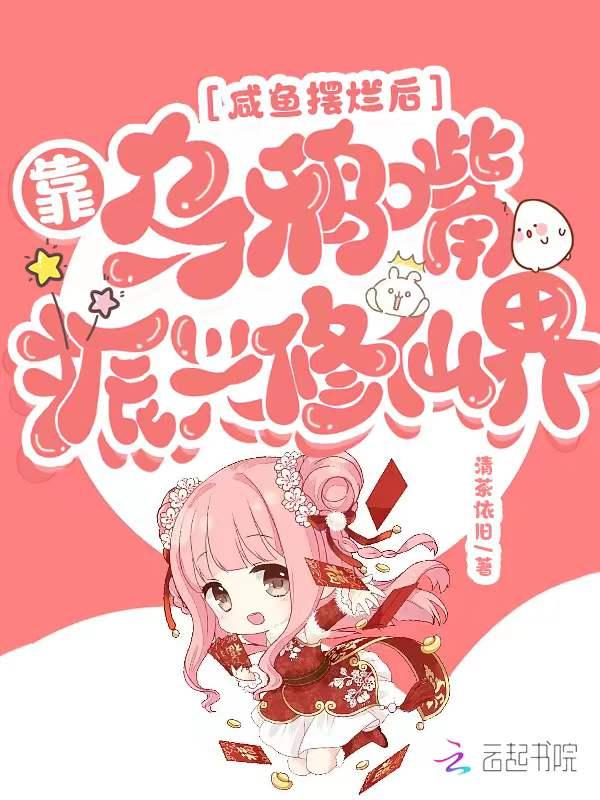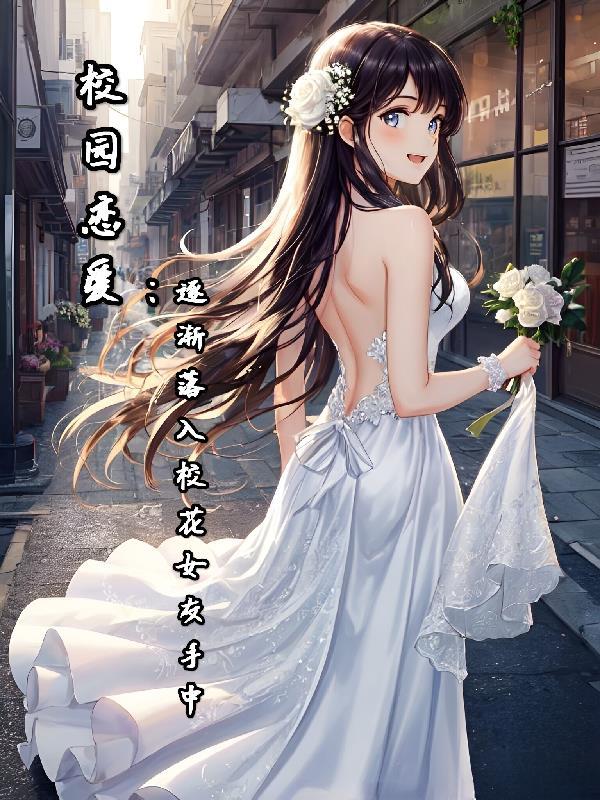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主公她今天造反了吗 > 渌水之战下(第2页)
渌水之战下(第2页)
随着一批批辎重入水,渌水西岸好像猛地长出了许多礁石。这时傻子也知道苏日勒是什么意思了。
这么多人的辎重,渐渐入水,这哪里是造桥,分明是要把这一段渌水填平!
这是十万人的辎重!所谓投鞭断流,不过如是。
砲车投石过去也于事无补,除了能砸死几个胡狗以外,只能替他们将辎重桥砸得更紧实!
景初握着缰绳的手不自觉攥紧,太史敬也频频偷眼去瞧景初面色。
如今,可如何是好!
他焦躁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正想劝将主下令撤离,不防景初突然唤他:“德枢。”
太史敬立即整肃容色,敬听吩咐:“在。”
“你千万要顾好天子。”景初微微偏过头,眼里是郑重和不容置疑,“绝不能让汉人的皇帝陷入胡人之手,否则史书之上,你我都难逃千古骂名。你听到了吗?”
太史敬只觉得背后冷汗滋生,勉力俯首以对:“岂敢负命。”
景初点点头,翻身跨上新得的枣红马,稳稳接住了侍从丢来的蟠龙枪。
“将主!”太史敬猛然抬头,声音绷得像将破未破的鼓,“您要去哪?”
他见景初孤坐马上,挺直的背像一杆清瘦的竹。
“我去会会苏日勒。”
战场上嘈杂的喊杀声充斥在耳畔,让将主的话都显得渺远。
他见将主抬了抬枪,好像想冲下矮坡,却又勒了缰绳。
他俯身拱手等着将主吩咐。
但景初头也没回,只丢下了一句:“照顾好悯之。”
话音未落,那匹乌力吉的枣红马已载着新主和她的银枪远去,留在原地的只有扬起的黄色的烟尘。
太史敬狠狠抹了把脸,把嘴边的“将主保重”这句话咽回肚子里。将主此去,是无奈之下的行险之举,是兔抗狮子时的殊死一搏。
她是怀着死志的。
他本应随侍将主身侧,可将主却把皇帝和悯之托付给了他。他不能走。倘若事有不协,他要保着皇帝逃走。
可那是十万人啊。
那样的茫茫人潮中,洪流若要碾碎一个人,只怕连骨殖都留不下。
他眼有点红,沙子好像迷眼睛了。
苏日勒的身边,阿勒部的头人特木其见到大局已定,谄媚地笑着恭维苏日勒,这笑容却因为脸上的一道鞭痕显得有些狰狞:“圣明无过单于!此次擒杀了那齐国的皇帝,得了齐国皇子许的土地、牛羊和奴隶,从此草原之上,哪还有人敢不服从单于的号令!”
苏日勒淡淡瞥了一眼特木其,“你什么时候也跟齐人学了这哈巴狗的样子。”
特木其笑脸一僵。
他感觉自己的胸腔中窜出了无边羞恼与怒火,烧得他脸膛通红。
可他丝毫不敢表现出怒意,只是腰弯得愈发低了。
他怎么敢呢?他不止代表着自己,更代表着阿勒部的近万青壮。此战之后苏日勒崛起之势无法遏制,几千青壮想在屠哥人的阴影下生存,怎么能不讨好屠哥人的单于呢?
“单……单于玩笑……小人……小人……”
小人本就是您马前的一只狗啊!
理智告诉他应该要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