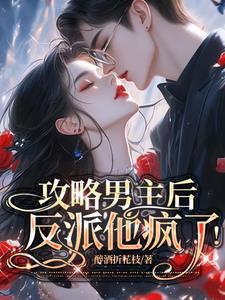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征途实录:启航1926 > 第245章(第1页)
第245章(第1页)
“所以西方那种选票制决定一切,本质上与他们说的民主自由恰恰相反,因为有了投票就有了无限背书,这是实质上的威权和专制——选出了垃圾政权你也得认嘛,我是选举产生的我怕谁?反正无论做什么还是不做什么,都已经是合法的,一上台就已经万事大吉了,那还努力那么多干嘛?做得越多,反对党抓到的小辫子就越多。”
“选票神圣化更是可笑。选举就是一场营销,选举不是设定国策,而是如何充分地攻击对手,让人们充分感觉到对手比自己更差。赢得选举的人,通常不过是善于骂人,善于攻击对手,善于表演,粉丝量更大。至于能不能治国,谁关心?”
“所以我们观察最近几十年的西方政坛,可以看到多数的西方政府,在选票上台后的表现,是庸碌而摆烂的,这是他们越来越落后于我国的根本原因之一。”
“西方的这一套,说白了就是“上帝附体”的宗教化,先把民主神话,再把选票制神话,这不就是一套落后愚昧的宗教教义吗?你要是稍有异议,那就是亵渎上帝,是异端,是罪孽。至于这一套能不能治理好国家,能不能推动社会、民族和国家的进步,那根本不在考虑之内。”
“以英美为主的这一套民主自由,本质上是反社会化的,它们会有促使社会解体,退回原始社会的倾向。英美之所以极力推崇民主自由,就是心里明白它们既然自己有这类天性和倾向,反而故意利用这种天性和倾向,去实现其基本的对外战略——制造其他国家内在的矛盾和解体。”
“但是,这种非社会化功能,并非只是会作用于其他国家,也会在各种条件下,反作用于其自身,反噬自己,甚至最终作用于其国家社会内部的能量会更大。”
“英国衰落后,日不落帝国不断向彻底解体发展,所谓的英联邦再有几十年,恐怕将荡然无存;欧洲一千多年也无法统一,留下了一堆小国;美国如果衰落而内卷,最终也必然分崩离析。没有全过程只有最初的民主口号嘛,那一旦内部矛盾上升,不崩待何?”
“如果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理念和基因,就是非社会化和内在解体趋势的文明,怎么可能成为长期延续的先进人类社会文明?”
“这就是西方民主和自由的本质矛盾。将民主完全前置化,就是一种本质上反民主、阻碍民主的行为。将自由绝对化,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如果只要自由就是结果,只要自由就不再需要其他,那就会极大限制对自由的利用。自由就很难再有真正积极的社会化意义和价值。绝对化的、前置的民主,就是一种专制。因为你投票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你可以上大街去反对,但有意义吗?”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西方的当下趋势,就是越是毫无意义的,不能给社会增加利益性的自由,越是被当成纯正的、更高政治正确的自由。甚至越是反社会利益性的自由,越是体现出纯正的前置上帝附体的自由,越是政治正确。当年民主自由选出了希特勒,未来也会如此。”
袁浩云和赵云腾都怔住了,领袖的思想仍然极其犀利。
三人讨论了一阵后,李思华想起一件事情,她对袁浩云说道:“我最近有一个想法,或许有点疯狂,但提供给中央作为未来发展的参考。”
袁浩云的神色严肃起来,但知道领袖这类“狂想”,可是创造了不少的奇迹,很多至今在国民经济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你们应该注意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国大规模的传统基建时代,大约到2000年左右就结束了。”
“包括高铁在内的铁路,已经完成115万公里,还有35万公里,十几年肯定能完成;公路已经完成1080万公里,还有370万公里,十几年也差不多了。水电水利,或许会延长个101年左右的时间。推而广之,在多数的传统基建领域,都可以明显体会到这种大趋势,即大规模建设的时代,已经进入尾声,大约再有二十多年,多半会结束这个时代。”
“这并不是件坏事,共和国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让我们有了国际一流,不,是全球最先进最完善的基础设施,支撑了各个产业领域的大发展。”
“但大家都知道,我们经济发展,一向靠的是两条腿走路,一条是产业,一条是基建。未来难道只剩下一条腿吗?”
“当然,基建并不会完全结束,新基建会替代一部分,例如交通上的管道轨道系统,通讯上的移动通讯系统会一代代的迭代等。而向海外社会主义国家,转移基建产业能力,也能提供一部分的支持。但无可置疑的是,基建的总规模,尤其是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会不断缩小,这使得未来经济增长的力度和速度,会相应下降。”
“显然,高明的策略,不应该是放弃大基建,而是创造新的有经济效益又有规模的新基建。这就是我这个疯狂想法的来源。”
“我的设想是,在传统大基建时代结束的同时,开启一个“户均1000平米全民科技别墅化”建设的新时代。”听到1000平米这个数字,袁浩云和赵云腾都是目瞪口呆,难怪领袖说这是一个“疯狂”的设想!
“这个设想,是与网络社会、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远程办公、胶囊快速自动交通等未来科技的发展分不开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土地资源,人口出生率已经在下降,但我们还是宽裕点来算,未来算24亿人好了,按4口人一户,那就是6亿户。户均1000平米,如果是3层楼的别墅,占地大约算370400平米建筑率,例如1层380平米,2层380平米,3层240平米,这都没算地下室。占地1000平米去掉建筑的380平米,还有620平米,是绿植、道路和辅助设施占地。6亿户占地就是6000亿平方米,折合60万平方公里,显然,我们国家是可以提供足够的建设用地的。”
“每户一套别墅,重要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高级的居住条件。这套房就是一个未来产品和科技的载体,能够承载无数未来科技产品的存在和消费。”
“例如每户可能要配套35个机器人,配套2个胶囊交通自动车,配套一个综合运动室、一个游泳池、一个娱乐室等等,甚至可以设置环屋跑道,足够一家人折腾的。1000平米加上地下室可能达到1300平米以上的空间,几乎可以容纳一切的家庭智能化配置,这显然是现在100平米空间的组屋所不能比的,100平米能摆多少东西?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将原来的单位面积放大10倍的新组屋计划。只有这样的新空间,才能让未来发明创造的几乎大多数智能设备,能够完全地应用并被家庭和个人市场消费。”
“所以这个新组屋计划,并不是完全的基建,而是基建+产业的复合体,在发展新组屋的同时,配套家庭生活的各种产业,也会蓬勃发展,例如机器人,至少可以多上几倍的市场吧?造游泳池的,肯定是以前上千倍的市场,而体育和娱乐产品,就更不用说了。”
“这里提到的胶囊车,是出行用的,每部胶囊车,可以载两三人,胶囊车自动驾驶,到了交通站点后,被自动编组,组成胶囊列车,统一输送到目的地或者中转地后,再重新解散或者编组,最后的一公里由单独的胶囊车自动完成。未来发展到高级阶段,可以每个人一部胶囊车成为标配,包括小孩子。”
“对于这个设想,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人民是否负担的起的问题。但我仔细地思考以后,觉得是有可能的。”
“我找人了解过,由于建筑科技和建材产业的发展,如果是国家组织,用微利保本的方式,按照目前的价格再考虑通膨率,20年后的价格仍然可以将建筑成本,压缩到1000元平米出头,加上其它一些配套设备,总的建筑成本,可以控制到2000元平米以下,这样一套房的总建筑成本,大约是200万左右。这种低成本,本来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势嘛。”
“主要的花费,大概还是智能系统,未来可能的成本,大约与现在的一台中级车相似,例如3个机器人和2台胶囊车,就需要130万元左右,如果是5个机器人加2台胶囊车,大约要200万左右,所以其它杂七杂八地加起来,一个完整配套的家庭,恐怕需要500万左右,加上房子,那就是700万元,宽松点算800万元好呢。”
“4口之家双职工,如果是10年收入作为一个比较适合的数字,那么每年两口子需要收入80万元,家庭收入中位数与人均GDP有统计上的可比性,80万元的家庭收入,那么人均GDP也要达到80万元,这是一个人均收入相当于人均GDP25%的水平。”
“我们1985年的人均GDP,大约是1。7万元,离开上述的目标相差是不到50倍。从时间线来算,20年之内,仍然是传统大基建的时代。假设我们从2010年左右开启,用5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这个新组屋计划,那么中位时间即前20年加上后50年的一半25年,总共45年左右。45年我们的人均GDP能不能翻近50倍?”
“我们把45年分成两段,前面的21年假设7年翻一番,后面的24年假设8年翻一番,2的六次方,是64倍,这还超越了需要的50倍。”
“所以人民有没有消费力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能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以及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使得人民群众一直能够有比较均等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