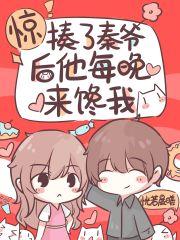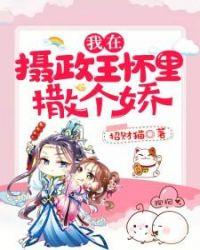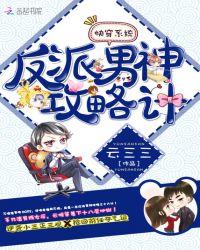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征途实录:启航1926 > 第237章(第2页)
第237章(第2页)
蓝色小药片被FDA压制了2年不能上市,无非是美国的医药集团不愿意而已。但中国的反击很犀利,这个阶段美国的所有新药,在中国全部被卡,而且中国正在考虑废除对美国的药物专利,因为美国人首先不遵守平等的规则——既然中国允许美国的药物,合法合规地在中国上市销售,那么反过来也一样,美国人能制造障碍,中国人就不能了吗?最终美国的医药集团,被迫屈服。
说起来,对于中国市场,是美国大型医疗设备和药商最能用“又恨又爱”来形容的市场了,爱的当然是市场规模,如果一款药物或者医疗设备,能够被许可销售,盈利自然是庞大的。恨的则是中国对美国药物的审核,越来越严格,还有在医疗设备上的科技反超。
中国人总是认为西药有严重的副作用,因此西药通常必须有在美国或欧洲国家,5年的实际使用数据,这些数据并不是单单由药厂提供,中国人会广泛调查,如果副作用大了,一定会被拒绝,中国人认定这些药厂都不是好人,认为他们总是试图隐藏化学药物包含的严重后果,往往让西方药厂,感觉中国人是把他们当作潜在的犯人,而不是救死扶伤的善人。
这种威胁是现实的,因为药厂如果疏漏了汇报副作用,靠着隐瞒的手段让药品在中国开始销售,最终总归会被发现,中国的医疗机构会记录每一种药物使用的结果,通过他们的“大数据分析”,确定药物是否有严重的副作用。一旦确认,惩罚是极为严厉的,不但在中国的全部收入被罚没,还要追究药厂管理层的刑事责任。
在1977年发生的“辉瑞事件”,让所有的美国药商想起来就不寒而栗。辉瑞当时有款化学药,就是采用隐瞒副作用的方式,登陆了中国,在最后被发现造成数十人死亡后,所有还没有汇回美国的收入全部被没收,辉瑞中国办事处的责任人员被判刑,而中国还要求辉瑞缴纳罚款2亿美元,并要求辉瑞负责这个药物的一个副总裁,以及几个其它的关键人员,到中国接受法庭审讯。
辉瑞拒绝支付罚款,而这几个人当然不敢去中国,美国法院体系,也驳回了中国要求的引渡。结果在超过了中国规定的3个月限期后,被中国缺席判处死刑,认为他们是谋财害命。那几个人都在一年内,各种离奇地死于非命。所有药商都知道此事——这是中国人的警告,美国政府也保护不了你们。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吗?
美国政府的抗议,也被中国严厉地驳回,认为FDA放行这样的药物,是“美国之耻”,应该自己反思,美国凭什么为一个谋财害命的公司出头?是何居心?此事之后,辉瑞被中国永久禁入,被冠上了中国“黑心公司”的排名榜,这导致辉瑞声誉大跌,股票大跌,甚至在美国,这种药物也被抵制,被美国人各种起诉——美国人自己又不傻,搞得辉瑞狼狈不堪,公司实力因而大损。
在那以后,有些美国药物公司,就不再愿意做中国生意,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中国也不在乎,自身药物的发展,也越来越块嘛,而且有些美国药厂是舍不得中国市场的,反正提供真实数据和对副作用的说明后,就没风险,有风险自己先拦下来。
医疗设备商,原来是最快乐的,设备嘛只看质量指标,谈不上什么风险,唯一的不快,就是中国的本土设备商,在科技和生产上追得飞快,到七十年代后,其实只能是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才能在中国大规模销售了。
中国这样的GC体制,使得他们在其它国家,那套对关键人员塞钱的营销模式,根本起不了作用。一旦同等水平的中国本土设备,出现并通过国家审核,每个医院中采购的这类设备,就强制必须有80%是国产,没有买够国产之前,根本不能买进口货,除非医院能够提供国产品质量低劣的有效证据,那政府机构会反过去惩罚厂家。中国人这一套是很有效的,医院都是公立的,而厂家也都是国家有股份的混合制企业,他们拥有充分的权力。
最近五年,医疗设备商开始感到了恐慌,因为中国ICT科技领先全球,而医疗设备正是ICT科技高度快速应用的一个大行业,缺乏了中国ICT科技,产品就会变得落后,而中国的竞争对手们,正在利用这个优势,不断地缩小他们与美国医疗设备行业的技术差距。
总之,中美医药产品的贸易,是中美贸易中,现在最复杂的一个领域,蓝色小药片最后被FDA通过,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已,双方斗争得很激烈,但美国企业们也不愿意失去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虽然美国的医药消费,占到全美GDP的15%,而中国的医药消费仅占GDP的6%,但由于中国GDP是美国的5倍,因此中国的医药消费市场,妥妥地相当于美国的2倍,美国医药商再到哪里去,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超级大市场?
若干年以前,美国医药商企图以“自由贸易”的理由,推动中美医药贸易的自由化,但被中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而且是嗤之以鼻,说你们美国人谈自由贸易,那就先取消了“巴统”再说,本身对中国加以多重限制,谈个鬼的自由贸易?说白了中美互不信任,所有的贸易,只能是根据根双方随时可能调整的贸易协议来执行,医药当然不例外。所以美国医药商的努力,只能是折戟沉沙。此后他们多年的努力,也没有能改变这种状况。中国是全球经济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其它国家的霸权,对中国根本不起作用,他们也只能守规矩。
医药,现在仍然是美国相对中国有着较大出超的不多的产业,但美国的医药行业分析员们普遍都认为,未来美国医药业,只能是通过创新的设备或者药品,才能在中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因为中国本土的医药产业,可不是其它国家能比的,不但现在规模已经是全球之最,而且科技进步速度也是最快的,追平美国的日子并不遥远。
说起来,新中国的医药事业,大约是诸多科技和产业中成长最艰难的一个,到现在为止,在先进程度上,仍然落后美国一筹,被国家认为仍然需要10年左右的努力。
在1939年新中国建国的时候,中国的医药事业只能说是刚刚起步。解放前缅华和西华时代建立起的医药事业,仍然是非常薄弱的,那一年统计,包括留学归国和犹太人在内,再包括国内的一些水平较高的医生,西医高级人才不过只有1。5万人左右,而到1940年统计出的高水平的中医师,大约只有八千人左右。其余的医护人员虽然有20多万,但按照现代标准,几乎都是不合格的。
在西药上,西华时代解决的,不过是战争导向明显的磺胺等十几种重点化学药物仿制,大量的普通药物,只能等到建国后开始发展,就连青霉素,都是1944年才试生产成功的。
所以这个领域的底子,是真的薄。建国后在1940年制定的医药发展策略,可以被称为“三个十五年计划”,规划每一个15年上一个大台阶,逐步追上当时先进的美国和苏联医药体系。
最初的时候,主要参考的是苏联的医药体制,美国那种富人和金钱优先的昂贵医药费体制,当然不会被考虑。
一直到赫鲁晓夫时代末期以前,苏联的医药体制,对底层人民而言,完全是最慷慨最优秀的体制,恐怕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医药体制。
1936年通过的苏联宪法第42条明确规定:“国家保证对所有居民提供免费的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你没看错,对全民免费医疗!写入宪法!这绝对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创举!关键是免费是真的!
而且苏联的免费医疗,当时确实是真正的免费医疗,可不是后世那种大部分国家都宣称实行的“免费医疗”,结果却是垃圾一样的服务体系,只能治一点最基本的小毛小病,医护的水平都很差的“免费医疗”,其实后来各国所谓的免费医疗,无非是要看好病,就去私营医院花大钱,否则只是“看病”而已,谈到真正治疗,就只有呵呵了。
例如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最负盛名的英国“免费医疗”,当初就是对苏联体制的模仿,不过虽然最负盛名,其实对穷人的免费医疗,也只是一个象征而已,在原时空新冠疫情的时候,英国这个医疗体系的破功,足以说明其真实的成色。
苏联的免费医疗,包括三大部分:医疗服务制度(免费满足居民的一切医疗服务,免费提供病人住院的治疗费和诊断费)、劳动保护制度(改善生产的卫生条件、安全技术,消除工伤和职业病)和疗养制度(发展疗养设施,为工人和农民的休养服务)。
正因为这样玩真的,所以苏联的医药事业进步很快,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免费医疗覆盖后,新生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各种传染病大幅下降,人口寿命迅速提高,苏联人的预期寿命,在1960年代中期,达到了峰值,男性64岁,女性73岁,与当时的西欧平均数大致差不多,这可是在苏联,一个嗜酒如命的国度!
但是李思华在建国初期,建构新中国自己的医疗体系的时候,她却否决了完全遵照苏联的免费医疗模式,原因很简单——第一是当时中国还玩不起;第二是这种体系到了老年化的时候,负担太过沉重,全靠国家必然让财政负担沉重不堪。所以中国最终采取的,是“成本导向型低医药费用+个人医疗保险”的体系,大致是学习了苏联的低成本低费用,又学习了西方的个人医疗保险。
李思华知道,原时空苏联的免费医疗体系,到七十年代就逐渐开始衰败,原因除了干部阶层逐渐腐朽,导致医疗阶层化以外,苏联逐渐负担不起了这个体系,更是重要的原因。
开国阶段,人口年龄普遍年轻,但随着和平时代的延长,人口平均年龄逐渐上升,医疗费用的需求就开始几何级上升。如果苏联在人口平均年龄35岁或以下的时候,确实可以轻松地负担得起全民免费医疗,但是等到全民平均年龄45岁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个无法填平的超级大坑。
所以,虽然“全民免费医疗”非常GC主义,非常政治正确,但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还是不能跳这个大火坑。
苏联医疗体系中,真正被李思华看重的,是两大重点。
第一个,是通过完善的全民医疗体系,实现“治未病”,治疗在发病之前,降低发病率,其实才是真正降低的医药费用。
苏联在卫生工作中贯彻预防思想,极大减轻了社会患病人数和病患严重程度;通过预防数十种常见传染病和流行病,并提供全民接种和免疫;强制年度体检,以及早发现疾病以便医治;高度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并强调劳动场所和生活场所的环境卫生;开展全民卫生运动,注重个人卫生和水源、土壤等清洁,尤其重视对青少年的健康保护;大力推动全民健康教育,发展体育运动,提高了国民身体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