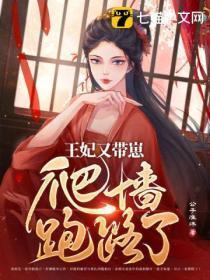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征途实录:启航1926 > 第200章(第3页)
第200章(第3页)
李思华叹了一口气:“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最困难的地方,如何长期地一贯地保持革命热情,尤其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面对经济利益的诱惑,来保持革命者的初心。”
“我党到目前为止相对苏联的幸运,不客气的说,在于主席您与我是开国的第一代,威信还够高,建国以来压制住了类似的“官僚冲动”和官僚利益集团的形成,搭建了远比苏联更完善更周密的预防策略和组织,使得我们的领导阶层,还没有变成苏联那种官僚阶层。”
“但是人亡政息,我们终究有要去见马克思的那一天。未来会如何?我们从今天开始,还是要不断加强人民的思想教育,赋予人民相应的权力,让人民成为我们对抗官僚化的防火墙;也要加强机制防范,最重要的是搭建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实体系。一个脱离底层人民的官僚阶层,必然走向变质,走向人民的反面,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主席深以为然。他接着说道:“你以前说得很对,对多数人,不能只讲精神激励,还必须有物质或者其它激励,否则时间长了,精神疲惫了,也就没有了激励效果。但是所有的激励不能是特权,不能是长期固化的经济利益,后者也是特权中特殊的一种。但是不搞苏联那种干部特权,我们就要完善中国特色的干部激励体系。”
“干部配车、津贴、住房补贴这些,都不是好的激励,因为只能升不能降。短期是有激励效果的,但那是一种不符合革命者信仰的负向激励。长期就完全是负面的,有了这种特殊特权,干部们就会倾向追求更多的特权,要更多的经济激励,如果取消掉这些特殊待遇,他们就牢骚满腹,消极怠工甚至心生歹意,赫鲁晓夫倒霉就是这样。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会越来越反感干部,谁还会认为干部与老百姓是同一个阶级,是老百姓的代言人?搞笑嘛。做事就只是做事,不能是为了高人一等而做事。”
“所以我对干部,是赞同间接激励,而不是直接的长期经济激励。直接的长期经济激励,是短期猛药,却是长期毒药。”
“当干部获得的报酬,原则上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多劳多得,做出了贡献,应该获得报酬,但报酬未必是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是其它方面的激励。我觉得那个社会贡献分体系是很好的探索,在这些方面应该多加努力,探索出更多新的模式来。总之,我们的激励,应该与干部革命的思想、方向和努力结合起来,而不是与职位、权力相结合。否则只要人上人这一概念仍然存在,几乎任何制度,都会被这一思想侵蚀。”
主席提到的社会贡献分体系,在建国初就已经提出,从西元1951年开始试行,从第三个五年计划(1956年开始)正式执行,目前也还在不断完善中。
贡献分或者说贡献值体系,是考虑到人对经济利益的需求无非是两种,生存需要和享受需要,贡献分就是用来引导人们正向地去实现需求,而不是往歪门邪道上努力。用贡献值来引导人们自发的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并以此换取奖励。
体系中所说的贡献,是无论事情大小的,打扫卫生是贡献,科研突破亦是贡献,甚至垃圾分类,节省节约,都是对社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贡献值则是将所做出的贡献具体量化。换而言之,只要是做正确的事,便是做出贡献,便可以获取贡献值。至于什么什是正确的事情,是通过贡献值委员会与民众一起,不断地讨论,总结,制定,并纳入贡献值的设定,每年都有多个听证会,来调整和完善贡献值体系,而个人获得的贡献分,是一切公开的。
所以作为服务公众的干部,就类似科研人员,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更多的贡献分,贡献分的高低,决定了享受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先权排序。例如现在医院医疗资源还比较紧张,贡献分高的就是优先使用;例如组屋购买,同样是贡献分高的,优先购买和挑选房屋。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直接的经济奖励,贡献值直接影响每年的人民分红的份额比例。
这种公共服务优先权,当然也可以说成是一种特权,但这种特权,是由贡献所决定的,而不是所谓的金钱、地位和阶层。
贡献值不是固定的,而是浮动的,以此来避免人们一股脑地对贡献值高的事物和行业一拥而入,而对贡献值低的充耳不闻。能做出更多贡献的人,也自然是在某个领域学艺更精、工作更努力的人,以此鼓励大家在百花齐放的基础上,学习进步。
贡献值系统当然不仅是奖励,也有惩罚,例如在社会上的作恶,例如赌博、斗殴、辱骂、伤害等,尤其是刑事罪行,贡献值都是指数级的扣减,而无期和死罪,自然是全部扣除。
所以干部想获取薪资之外的经济利益,就必须做大自己的贡献分。例如在经济发展领域上的干部,如果为当地发展成功发展了某项新特色产业,那获得的贡献分就很大,一次性可能是一般人的数十倍,自然每年的人民分红都是不少的,而在公共服务上也就有了优先权。
当然如果被发现是弄虚作假,那惩罚是极为严厉的,不仅是贡献分全扣,倒查追索,而且公职不保,甚至刑罚追究。
所以贡献分体系,让贡献者主要获得的不是金钱,而是服务。金钱易于激发人类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而贡献分则力图激发人类精神中的高尚性。
而且贡献分与金钱有一个最大的差别,那就是金钱可以遗传,导致富人越来越富,造成贫富差距。但贡献分只是追随一个人的一生,人死“分”消,每个人的后代,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重新积累。
中国的贡献分体系,在三五计划开始萌芽,而从1961年开始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在各地大规模地执行。这个体系要得到完全的普及和深入到每一个人,还必须等待未来在网络基础上构建的庞大且发达的计算与监控网络。所以在五五计划期间,还是比较粗略的,但起码在计算机单机登记和服务器存储的基础上,也能够建立起每个人的贡献值档案了。
主席对于这个体系抱着很大的希望。不过李思华自己的认知,是这个体系很有用,但也不可能完全解决激励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措施和其它体系来完善。贡献换服务,对于比较“心平”的干部而言,是很好的长期激励工具。但对于那些“野心和贪婪欲望”比较大的干部,恐怕谈不上有什么激励的作用,还是会动歪脑筋,想追求直接的特权和待遇。对这些人而言,什么都比不上把钱装在自己兜里。
贡献分体系,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干部流动和定期审查和审计制度等,这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中,都蕴含着一条原则,“透明与隐私相对性原则”,越是底层人民,没有公职和其它特殊收入,就越是有所谓的“隐私权”,而职位越高、收入越高、社会地位越高,那么就必须“透明度”越高,因为必须经得起各种调查审核体系和人民的监督,这是一种合理的对价,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任何事,那就不要做官、不要当干部、不要发财、不要出名,你可以当个隐士,没有人来烦你。
李思华自己更指望,通过建立这样一整套包含严密的若干制度的体系,劝退那些为了发财和特权的投机分子,让他们无利可图,无特权可用。而两三代新人下来,他们熟悉和接受了这套严密体系的管控和制约,习惯了“戴着枷锁跳舞”,那么情况就会好很多,社会主义的理想,也才能一代代地传续下去。
主席和李思华两人的讨论转向了中苏关系,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无疑是一个中苏改善关系的良好契机。
李思华指出:“主席,如果赫鲁晓夫10月下台,那么一个月后即11月,正常情况下,苏G会在莫斯科举行十月革命的纪念活动。虽然此前中苏关系紧张,但这个活动,苏联从来都是邀请我党参加,而我党也一直参加,所以这一次,我建议可以由李玉振副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利用这次机会,争取与苏联勃涅日涅夫政府改善关系。”
“勃涅日涅夫这个人,我前世后来的史学家,对他的评价都很低。但我不这样看,他有点像我国历史上的唐明皇,前期干得是不错的,从1964年到1979年,苏联从经济到军事实力的增长,可圈可点,一度让受到越南战争削弱的美国,不得不处于守势。他将苏联的力量发展到了顶峰,这一段时间内,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经济发展,是比不上勃涅日涅夫领导下的。”
“但这个人,现在虽然还未像原时空后来那样年老昏聩,但他也只是一个出色的官僚,不是改革家,不能开创新局面,只能维持旧体系。所以官僚体系不断发展,社会逐渐僵化,阶层逐渐固化。等到入侵阿富汗,苏联的国力就开始逐步消耗,开始走下坡路,这和唐明皇历史的后半段,其实有相似之处。”
“老实说,勃涅日涅夫这帮官僚,其实在意的是利用权势,享受苏联建设的成果,他们已经谈不上多少革命意志,剩余的只是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理念而已。但这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的点。我国的产品,无论是工业品还是食品等领域,丰富的程度不下于西方,甚至更超出,对于苏联的经济生活,是非常大的补充,完全可以扩大贸易,这一点是比较容易打动他的。而且他与我们素无恩怨,可不像我们与赫鲁晓夫之间,反复交锋。”
“苏联即将步入巅峰,这对我们而言,最近的二十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我国大量的产品可以出口苏联,包括东欧,大部分甚至完全替代西方产品的存在,也让苏联上层,可以取得降低民间和底层人民抱怨和离心倾向的效果。而我们也因此可以进口大量苏联的资源产品,例如油气和金属,至少可以降低我们国内资源的损耗,这是不折不扣的双赢。”
主席是历史大家,以前又听过李思华讲述过不少关于勃涅日涅夫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勋章控”的故事,对于李思华这个“唐明皇”的比喻,一听就懂,他笑着说:“你这个比喻不错,李隆基继承了武则天奠定了强大根基的唐朝,并在他的前期把唐朝推向鼎盛的巅峰,但在晚年,却搞得一塌糊涂,几乎丢了江山,唐朝因此由盛转衰。这个勃涅日涅夫,确实有点像。”
“这样吧,在李副总理去莫斯科的时候,让他各带一封我和你的亲笔信,哈哈,我们给足勃涅日涅夫面子嘛,他也好在苏G中央,有台阶可下。”
1964年10月13日,被克格勃从黑海之滨强制带回的赫鲁晓夫,在苏G中央全会上被迫辞职,从此被软禁居住。而本来苏G反赫鲁晓夫势力中两个最强势的人物,苏沃洛夫和谢列平,却为争夺大位而陷入僵持,为避免两败俱伤,只好双方都退让,最后被勃涅日涅夫捡了便宜,大家都同意让勃涅日涅夫,出任新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而他的亲信,柯西金成为了部长会议主席(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