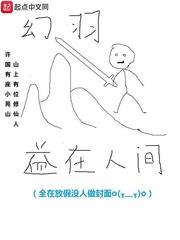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征途实录:启航1926 > 第185章(第3页)
第185章(第3页)
五、不要把一个具备某种产品特质的品牌,应用到与之不相干的其它产品上。
其实对品牌的要求是多方面的,但李思华觉得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能做到上述的五点,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文章中,她把品牌和名牌的重要性提得很高。指出这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市场竞争中,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重要一步,有了成熟的品牌,才有成熟的企业,国企必须补上这一课。
她尤其强调,品牌可不是狂砸广告费,品牌是企业用综合的价值体现出来的。国企也不能容忍过高的广告费比例,目前必须控制在营业收入的8%之内,而且要严格审计和接受调查员的全程监控。至于私企,超过营收8%以上的广告费,就不能在纳税基数中扣除。
强调品牌,也不是允许各种产品去定一个很高的价格,用“品牌”来糊弄老百姓,试图取得高额利润,物价部门仍然要对品牌产品的品价格进行严格监控,过高的价格必须压制。我们合理允许品牌的存在和发展,可不是为了让企业牟取超额利润的,而是为了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她尤其反对强调身份地位的所谓奢侈品品牌,对于海外进口的产品,属于奢侈品类别的,要征收高达销售收入80%的收入,作为“奢侈税”,国人出国购买这些奢侈品的,回国将因此交纳相当于购买价格4倍的“奢侈税”。国家将推出奢侈品清单,清单之内的产品发生销售,就要纳税,她将奢侈品称之为“精美包装的骗局”,其收入来自于虚荣人群的“智商税”,被骗了还以为自己有品位。
她同时还宣布,在国家市场监督总局下,设立广告监督管理司,对全国的广告进行监督,一旦发现广告违规,必须对企业进行惩罚。一些特殊产品,例如烟草和奢侈品不允许发布广告,而白酒等的广告必须事先报备。
李思华尤其强调发展工业企业的品牌,工业企业与普通企业不同的是,更多的品牌针对是自身的企业,就像是原时空的华为或者长虹,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产品。企业的名字就是品牌,就是品质、创新、先进等一系列价值的体现。而对于传统的老字号例如全聚德等,她一方面要求要保持一贯的品质,另一方面又告诫他们的品牌虽然传承久远,但有声誉也有负担,还是初级的品牌,必须与时俱进。
总之,不能不重视品牌,但又不要神话品牌,尤其是品牌的重要性还是在于传播与实质产品的一致性,而不是所谓追求品牌的忠诚度或则情感度什么的,那都是商家的吹牛,消费者有那么傻才怪。
李思华的这篇文章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可以说全国由此开启了品牌发展的时代。而在国外也很受关注,西方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开始很新奇,觉得GC主义的国家也会发展品牌?但很多熟悉李思华的人开始纷纷指出,李思华可是发展品牌的大行家,当年她在美国发展的多个品牌,到现在还是美国的著名品牌呢,人家是真正懂行的。
国企的重视是不必说了,而国内私企也非常受震动,他们都知道李思华当年在美国的“辉煌历史”,可没有谁敢说,自己比总书记更懂企业经营和品牌经营,学习品牌战略的热潮由此开始。
当然,李思华可不会相信,单靠自己一篇文章,就能让中国的品牌发展起来,她很快开始推动组织一个国内的品牌和广告体系。
一个是基于商标法的品牌保护体系,这是用来对付假冒伪劣和品牌侵权的,人家辛辛苦苦做了广告,有的人就想中途摘桃子,那可不行。
一个是品牌排名体系,开头有人提议组织专家学者来对品牌进行考评,被李思华直接否决,她轻蔑地说:“他们懂个啥?”
在她心里,这些人都是些象牙塔里没有在市场一线战斗过的人,本质上哪有评判的资格?所以她要求建立一套客观系统,是用品牌产品销售额、利润额、百万人随机知名度和美誉度调研、负面评价调查等,形成整体的打分系统,来决出最后的优胜者,每年会公布品牌优胜榜单,例如总体品牌榜单、行业品牌榜单等。
再一个是品牌评价体系,对品牌的价值和信誉,进行规定算法下的量化评估,可以计入企业的无形资产。
以上的体系,再加上一些其它体系,就是李思华提议的以发展自有自主为特色的“品牌建设十大体系”。
李思华发动的这场“品牌运动”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企业界和商界的层面,在西方也激起了不少涟漪,例如美国著名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佛利德曼,就与主张放任自由主义的哈耶克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辩。
其实这两个人都可以算是二战后,反G色彩强烈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区别不过是佛利德曼强调货币,而哈耶克强调经济的“自由”罢了。
对于中国的品牌运动,两人的观点分歧不大,都认为社会主义搞品牌是不行的,品牌是一种“私人运动”、“个性表达”,与社会主义强调集体与整体,是格格不入的。品牌是企业的一种高效率运动,而社会主义集中决策,没有市场经济中的分散决策灵活,所以社会主义,不可能有高效率云云。
但是佛利德曼认为,中国推动品牌运动,将导致中国资本主义力量的扩大,这必然会削弱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但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体制,也会对品牌的负面性起到一定限制,他举了个例子——在华盛顿的一座大楼里,一些政府雇员正在整天工作,试图制订和执行各种计划,用美国人的钱劝阻人们不要吸烟。而在另一座距离不太远的大楼里,另外一些同样具有献身精神并且同样努力工作的雇员,整天工作,以便用美国人的钱,补助农场主们去种植烟草。美国的这种精神错乱,不太可能在中国发生。
哈耶克对社会主义是完全仇视的,所以他对佛利德曼的这种说法严厉批驳。他的说法是,能保证人的自由的“自然秩序”,才是一种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所以西方的市场经济,才是最合理的制度。社会主义的制度就已经不对了,怎么可能有对美国的品牌优势?
这一通乱战,导致很多其它美国经济学家也加入,美国经济学界,一度热闹非凡。
李思华读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却只是感到啼笑皆非,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者,对于中国真正的经济体制,可谓是一无所知,在那里胡乱用中国的事,来说自己的理论而已,是“借题发挥”,其实与中国根本无关。
为了避免国内的思想混乱,她还是又发表了一篇文章,重复了她以前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定论:调放结合,顶层宏观调控,下层微观市场放开;顶层计划经济,下层市场经济。
她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中性的,是发展经济的工具,没有什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强调计划经济,是为了保障底层人民的利益,并不是所谓的这个工具专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利用市场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更有利于动员微观消费市场,并不会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强调市场经济,就对之忌讳。
如果把国家经济比拟成人,那么计划经济就犹如是在搭骨架、搭主动脉和主静脉血管,以及生长头脑。骨架好、血管通、头脑活,这个人才能成长为一个健康优秀的人;市场经济就犹如在骨架和主脉血管的基础上生长血肉和毛细血管,也不可或缺。两者的结合,才是王道。美国那样的完全私有市场经济,以及苏联那样的几乎完全的公有计划经济,都过于偏颇,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在文章中她还嘲笑了哈耶克和佛利德曼,说哈耶克的理论与其说是经济理论,不如说是讨好西方民众的心理安慰剂,满足他们对所谓自由和放任的幻想,在经济运行上则是完全的“空中楼阁”,西方任何一个有理智的领导人,都不会采用他这类在实质上胡说八道的理论。
而对于佛利德曼,她则感慨说佛利德曼的货币主义,是给西方开了一剂有兴奋剂功能的慢性毒药,由于其兴奋作用,恐怕未来会被西方领导人用来解决经济问题,通过宽松和滥发货币,来不断刺激经济,其实解决不了真正的经济问题,等到货币主义盛行的时候,恐怕西方长期的“滞涨”型经济危机就会来临——物价持续上升,但经济停滞不前。
文章的最后,她还恶作剧地说了一段非常刺激西方经济学界的话:“二战后的西方经济经济学家们,不过是自说自话,甚至自娱自乐。其研究动机,缘自现有研究纲领的内部逻辑、知识的沉没资本和美学困惑,而非出于理解现实经济运行机制的强烈欲望,更别提理解危机及金融不稳定时期的经济运行机制了……今天西方经济学的大师们,就像是我国民国时代的大师,看上去名满天下,但实质毫无贡献。”
如果说李思华的文章,在国内主要是厘清思想的话,这篇文章在美国和西方,尤其是经济学界,那就是海啸了,立即乱成了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