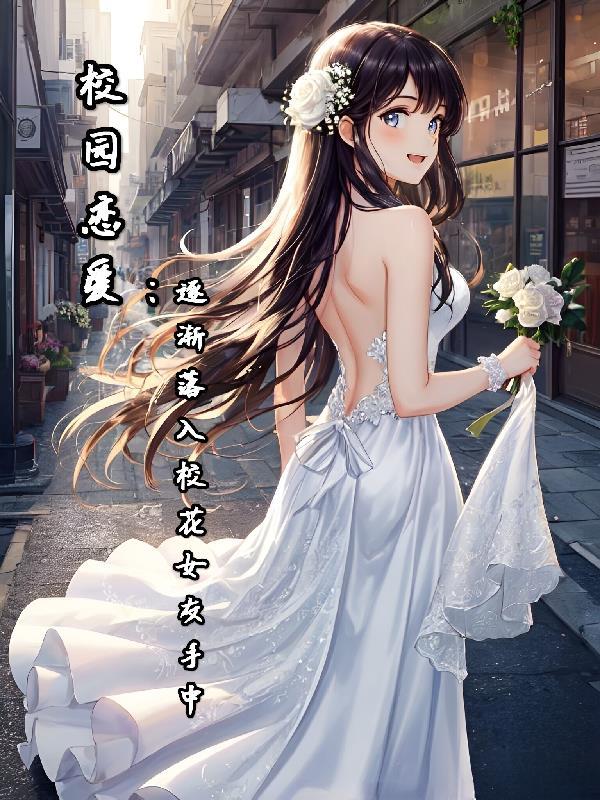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被迫失忆后和男神拯救世界了 > 退缩(第1页)
退缩(第1页)
祝庭手里没松劲的意思,看向时槿的眼神后知后觉地放柔了一点,不过并不多。他声音低沉道:“时槿,你先走开。”
再怎么说陈乐许也是他们一起并肩作战了七天的队员,也不能让她见死不救吧。于是时槿心一横冲了过去,站到祝庭面前说道:“快放开他!你把人搞成什么样子了你没看见吗?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吗?你在发什么疯?”
祝庭和她对视了一会,那双蓝色的眼睛里这次翻涌着比之前更多更多的时槿完全看不清的情绪,混合成夹杂失望和漠然的海洋,时槿被他盯着觉得自己像被一只被迫打断进食的野兽盯着,莫名发怵。
但她咽了咽口水,强撑着自己不在那眼神下退败,以一种自己都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和他悍然对视。
祝庭看出了一句话,就是她要把奄奄一息的陈乐许带走。
他开口道:“你要因为他和我作对?”
时槿哪想得那么多,就只是想要救人罢了。她这会看见陈乐许眼神都开始涣散了,血液还在顺着他磕破了的额头往下淌,她看着祝庭道:“我只知道他要死了,他需要治疗,现在,马上。”
祝庭目光在手里的陈乐许和旁边的时槿身上看了几个轮回,嘴角耷拉着不知道在想什么。
半晌,他终于松开了手,跟扔掉一个沙袋一样随意地丢开了手里的人。已经半处于昏迷状态的陈乐许失去了他这一支撑猛地向前栽倒,被眼疾手快赶过来的时槿揽着肩扶起来。
祝庭慢条斯理地掏出张白色的手帕,有条不紊地擦着手指间的血迹,看着他对面扶着陈乐许的时槿沉默不语。
时槿回避开他的目光,同样什么也没说,眸子里的亮光在看见刚刚的场景后都悄然熄灭了。
她没多留恋地带着陈乐许转身,搀扶着几乎不能自己行走整个人靠在她瘦弱肩膀上的陈乐许往吊脚楼的方向走了。
脚下踩过刚刚掉在地上的烤串和枯枝。
人声走远了,祝庭还站在原地,眼神看到地上已经又冷又脏的烤串。
时槿带着陈乐许回去时众人都吓了跳,都在问怎么搞的,是不是有其他队来挑事了。神色倦怠的时槿没了刚刚去找祝庭时的精神,疲惫地用有人刚刚来挑事但已经被她解决了的借口敷衍过去了。
她下意识地包庇了祝庭。
“谁啊下手那么重……这伤完全是虐待了。”乔思圆在旁边帮朱斯蒂亚和时槿打下手,喃喃道。
朱斯蒂亚是他们里面医学学得比较好的,自然挑起了帮忙治疗的大梁。本来热闹的气氛这会全然沉寂下来,所有人都如临大敌一般,除了在给陈乐许处理伤口的他们三以外其他几个人都在吊脚楼外严防死守生怕还有人再来挑事。
陈乐许身上的伤除了额头的几乎没有太致命的,正是这个原因让他没有立刻被淘汰。但他全身多处骨折加上各处没有太深入单纯折磨人的刀伤,刀刀都在最容易让人痛苦的地方,看上去很骇人。
这完全不像学员的手笔,反而像那些深谙审讯之道的老手或者虐待狂干出来的。
时槿给还算冷静的朱斯蒂亚递止血棉时的手都在微微发抖。
她在大家空出来给陈乐许治疗的屋子里待了没多久就忍不住跑到屋外了,浓重的血腥味在鼻尖挥之不去,时槿一手撑着屋外的木柱边弯腰一个劲干呕。
柱上挂着那盏暖黄色光的灯,这会照出的只有她一次次干呕弯腰看见的潮湿霉斑的地板。
门口守夜的叶瑞歌看不下去了走过来给她递纸,轻轻顺着她的背:“你是晕血吗?要水不?”
时槿眼泪都漫上来了,眼前祝庭冰冷的动作和那些残忍的伤痕闪回一样窜来窜去,她狼狈地摇摇头。
余光里看见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一步步地走过来,一副什么也没发生过的样子,身上沾染的血迹都已经被主人自己清理干净了。
时槿胃上泛出些酸意,下一秒她甩开叶瑞歌好心搀扶的手往屋里的厕所跑了。
“哎没事吧——”叶瑞歌在后面着急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