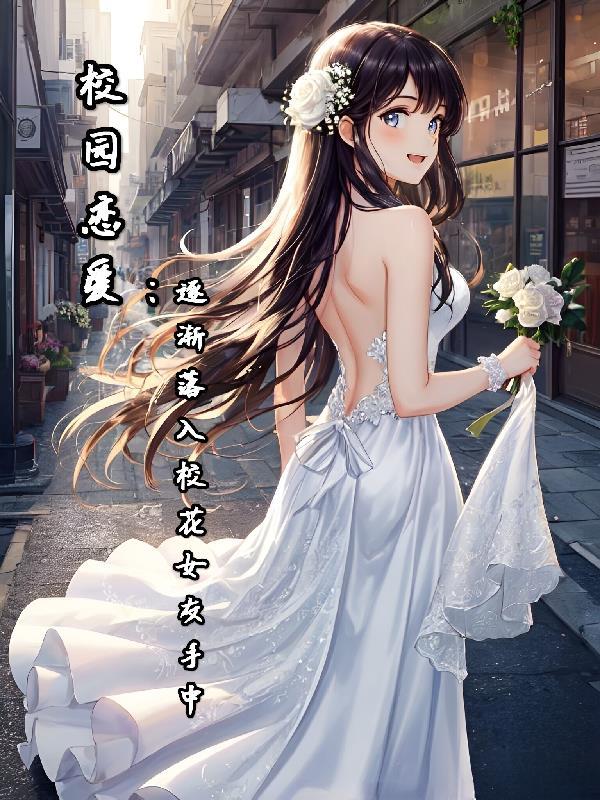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被迫失忆后和男神拯救世界了 > 退缩(第2页)
退缩(第2页)
祝庭已经走到门口了,面无表情地就要擦过叶瑞歌的肩时听见叶瑞歌抱着手臂开口道:“到底发生什么了?沈黎鸢说是看见你和陈乐许一起出去的,怎么回来只有他和时槿了?”
祝庭脚步一顿,投掷过来的眼神很冷,让人一下子意识到这个季节其实是主城的冬日的冷。
叶瑞歌挑挑眉,疑惑地和祝庭用目光对峙。
祝庭最终摇摇头然后直接往里面走了。
他略过正在一楼里屋忙忙碌碌给陈乐许疗伤的人径直上了阁楼,在沉默随着阳台微风流淌的房间里第一次主动按下了手环上长按提醒对方自己有紧急情况的按钮。
没几分钟,脸色很不好的时槿站到了他房间里,不自然地用手捏着她左手的手环,等着祝庭开口说话。
祝庭在她进门以后就把门关上了。他没有像前几天一样和时槿在独处时去和女孩很亲近地靠在一起,而是恢复了最开始他们之间不远不近的距离,动作间飞扬的衣摆擦过时槿的手。
他走过去坐在床沿上看着站在几步以外的屋子中心的时槿,眸子暗下来,笃定地开口:“时槿,你在害怕我。”
时槿被他戳中了心事,胃部又开始不适起来,身体反射地想吐。
堪堪止住后她摇摇头,下意识又往后退了一步,摇摇头很生涩地启唇:“为什么?”
简短的三个字包含了太多,祝庭一时不知道她是在问为什么觉得她会怕他还是在问为什么那样对并肩了几天的陈乐许。
他自顾自地按后一个回答了:“陈乐许应该是维格亚党派来监视我的,我在他身上看见了记号……”
时槿忽然冷笑了声,打断他的话说:“所以这就是你那么草菅人命的原因吗?被监视你不去找派他来的人而是这么折磨对方,多大的仇和怨啊祝庭。”
祝庭心被她的话拧成一团,他刚刚的确是太失控了,但袅晴和祝听潮的死、三年前那次针对白色大楼的围剿、血流成河的全是自己同胞的画面翻滚上来时他就已经被仇恨磨成尖刀了。
而这些时槿都不知道,他也不能在此刻开口说。
他只能微不可查地叹口气,不知道如何辩驳了:“我不动手的话,他们就会对我们动手。”
时槿意识到这里的“我们”并不是平时指代他和自己的含义,而是说的白色大楼。
她抬眸和祝庭对视,眼里悬悬欲坠的难以置信和痛苦被猝不及防的祝庭接过去了,她眼眶都红了,话语掷地有声:“那要是有一天这个人是我呢?你对一个和你并肩几天的人下杀手那么轻松,换做是我、是叶瑞歌、是你周围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吧?”
听到这番话的祝庭按耐不住地站起来走到她面前,捕捉到女孩想往后退的步子后猛的抓住了时槿的手腕。
时槿下意识想挣开,自己的他手里还留着陈乐许的血。
“时槿,你听我说。”祝庭心如刀绞,万年不变的语气都急切起来。他完全不懂要怎样给自己辩解了,只胡乱塞了把被他擦干血迹的刀到时槿手心,引着时槿拿着刀往他身上单薄的布料戳。
被迫拿刀的时槿反应大得吓人,她小兽一样在祝庭越来越用劲的动作里撕着嗓子尖叫了声,看着尖锐的刀尖在他腹部的布料戳出一个眼泪一样滚烫的口子,她哀求道:“你做什么!不要这样,放开我的手……不要,求你了祝庭,不要用这种方式,我不想伤到你。”
眼泪不知不觉地从她颧骨的雀斑滚下来了。
祝庭手上的动作顿住,他凑过去怜惜地吻时槿通红的眼睛,时槿却只顾着这个凑近的动作有没有让刀刺到他的皮肤,在被蛇信子接触般的亲吻里冰冷地颤栗。
祝庭止住动作,看着时槿无声地叹息:“我不会伤害你,如果真有那一天我会像现在一样亲手把刀递到你手里。”
时槿趁他力道松懈的瞬息用力挣开了他的手,刀哐当一声掉到地板上,泛出冷白的光。
时槿哑着声丢下一句话:“太过了,我承担不起你那么大的偏爱,祝庭,我真是一点也看不懂你,也一点不懂你们那些七拐八拐的事情,我只觉得你残忍。”
话语比刀尖更钝痛地划过少年的心脏,他敛着眸子沉默不语,意识到这可能是他们今晚的最后一句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