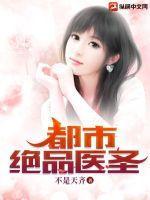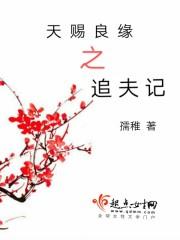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书签落处,你在页间 > 六十七 片语与沉光(第2页)
六十七 片语与沉光(第2页)
刘奕羲抬头看他,嘴角仍含着惯常的笑意:“能有什么事?不过是剧本微调罢了。”她的语气轻得像吹开书页的风,指尖却无意识地摩挲着袖口纽扣,那是她紧张时的小动作。
“真的?”他又问,身体前倾半寸,逼得她不得不仰头看他。她身上飘来若有似无的洗衣液清香,混着器材间的机油味,竟让他想起那些在片场过夜的凌晨——她抱着剧本蜷在折叠椅上打盹,睫毛在眼下投出扇形的影,而他趁她不注意,用圆珠笔替她把乱翘的发尾轻轻压平。
“嗯。你多心了。”她答得太快,快得像按了快进键的台词。祁祺望着她瞳孔里自己的倒影,那倒影太过清晰,清晰得让他心慌——从前她眼里的他总是带着柔光滤镜,像浸在蜂蜜里的月亮,而此刻,那倒影冷得像面刚擦过的镜子,能照见他眉间未褪的戏妆。
祁祺终究没再追问。他太了解她——即便心底海啸翻涌,面上也永远是风平浪静的模样,连睫毛颤动的弧度都像经过剧本校准。
可这分“克制”偏偏让他心焦。他怀念她从前会把润喉糖纸折成小船丢进他咖啡杯,会在他卡壳时笑到打鸣,而不是如今这般,用指尖轻轻拂过他袖口,说“没事”时语气淡得像杯凉透的茶。
风扇在头顶嗡鸣,他望着她发顶的小卷毛被吹得晃了晃,忽然想起她写过的台词:“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沉默,是我看着你戴好所有礼貌的面具时,我却无法靠近。”
喉间发涩,他别过脸去看墙上的场记板。上面写着“第37场陆绍庭的伪装”,墨迹未干,却像极了此刻的他们——一个在演若无其事,一个在演毫不知情。
直到她的脚步声消失,祁祺才发现自己攥皱了衣角。蝉鸣刺耳,他按住狂跳不止的心跳,头一次对自己向来精准的“分寸感”生出厌意——如果他能像戏里那样冲动一回,也许早就问出了那句反复打转的问题:“你到底在躲什么?”
如果她真的和他吵一架,他或许还能想办法哄哄她;可现在,她连“生气”的权利都收敛得完美无瑕。
这微妙的错位让祁祺在片场频频失常。对戏时,本该脱口而出的“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卡在喉间,竟鬼使神差地说成了“我要让他们。。。”;走位时,皮鞋尖总在标记点前半寸停住,像踩进了看不见的沼泽。
“卡!”导演的声音再次响起。祁祺这才发现自己又走错了位,剧本边缘被他捏出深深的指痕。刘奕羲抬头看过来,目光与他相撞的瞬间,他听见自己心跳如鼓——原来最让他慌乱的不是NG,是当她用公事公办的眼神看他时,他忽然不知道该用“演员祁祺”还是“祁祺”的身份,去触碰她眼底的云。
导演以为他太累了,叫他去歇一会儿,制片也贴心地递水、开玩笑缓场。
可只有祁祺知道,自己的心跳为何总在转场间隙突然失速。
他会在对戏时,透过对手演员的肩膀,看见她站在监视器旁与灯光师交谈的侧影;会在走位时,用皮鞋尖丈量与她之间的步数,计算着若此刻伸手,能否触到她被风吹乱的发尾;甚至会在导演喊“卡”的瞬间,下意识地望向她的方向,像候鸟寻找迁徙的坐标。
他的心就这样,被她眉梢的褶皱牵扯得七上八下。
那不是能靠健身挥汗排解的烦躁,而是像根细银线,从她眼底的雾色里穿出,绕过他的心脏,在每个对视的瞬间轻轻扯动。他第一次发现,原来“专注力”可以碎成这样——对戏时会盯着她指尖转笔的弧度出小差,背台词时会被她翻剧本的声音打乱节奏,甚至连打板声都能让他条件反射地望向她,生怕错过她睫毛颤动的细微表情。
这种牵挂深入骨髓,像她写进剧本里的“隐性伏笔”,平时藏在台词缝隙里,却在某个深夜对稿时突然显影。
此刻片场的大灯亮起,他望着她在人群中穿梭的背影,忽然明白自己为何总在NG——因为他的每个细胞都在叫嚣着想去触碰她的情绪,想知道她皱眉头是因为剧本还是因为他,想在她咬唇时递上一颗薄荷糖,想在她笑时告诉她“看到你开心我比你更开心”。
原来喜欢早成了心跳的节拍器,在镜头亮起时,只能把支离破碎的心思,全揉进角色的眼神里。
而刘奕羲这边,何尝不是困在雾里。
她并非不懂娱乐圈的花絮炒作不过是行业常态,那些被镜头放大的“氛围感”与网友笔下的CP故事,她早已见惯不惊。可偏偏轮到祁祺时,那些配着“天选荧幕情侣”标题的动图,却像细针扎进心脏——她介意的不是炒作本身,而是在他光芒万丈的职业生涯里,总有无数个“看起来很般配”的瞬间,轻易就模糊了她藏在剧本褶皱里的心事。
她清楚自己无权干涉,毕竟他从未越界半步。
可那些质疑总在深夜改稿时漫上来,像咖啡杯底的残渣,苦涩又清晰。
——“他是真的把我放在心里了吗?”
——“还是这段关系,从头到尾,只有我走得太近了?”
那些疑问始终悬在心底,像未标标点的台词,她终究没敢念出声。
就像她处理生活褶皱的惯常姿态——把情绪叠进袖口,将过往封存在分镜纸背面,连笔尖划过稿纸的力道都经过校准。
她最深的心事,恰似笔下那些沉默的角色弧光:
表面是平静流淌的蒙太奇,每个顿号里都藏着暗涌的潮汐,字缝间的留白里,尽是不敢落款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