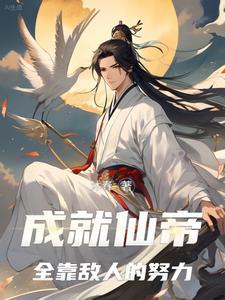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风前絮 > 田产朝廷清查(第1页)
田产朝廷清查(第1页)
次日卯时正刻,五品以上官员皆身着蟒袍玉带咸集东华门外。铜钟敲过三响,崇天殿正门轰然洞开,陶然目送着谢正秋的青衫身影随侍在御前黄伞盖后,才转身往翰林院公署而去。
他身位修撰,按制只需朔望朝参,此刻公署里对着《太祖实录》残稿待校,又有新朝建立一年的《起居注》需要熟悉,他便也不多想,独自去了。
朝堂之上,祝钦云提起朝中新封进士三百,遣往京中及各地为官,又加战事频发,国库吃紧,便议起官员减俸一事。
户部尚书钟辞章道:“陛下,前朝战乱时,曾主张裁减京官俸银十分之二以供国库,地方官员裁减十分之一。三月后,或有官员怨怼,则以低于市价的粮食布帛代替部分货币俸禄,以宝钞抵俸。若陛下有此意,惯可奉行此‘折俸’之制,若仿前朝例,京官俸银暂减两成,其中五成以新铸铜钱支给,三成折粳米,两成仍用宝钞,以渡过眼下难关。”
礼部尚书江雨杭道:“陛下,前朝发行宝钞滥无节制,原月俸十两白银者仅得二两,剩下八两皆以宝钞兑支,一两白银需值十贯宝钞,那八两白银却仅能兑换八贯,官员名义上领俸禄十两,实则不到三两,这七成缩减并无国库抵充,有无回收旧钞先例,官阶不高者,月俸折钞,仅足买薪数束。”
说着,他从袖中抽出一卷前朝邸报:“此份实录载,某知县月俸折钞千贯,竟换不得一斗粟米。当时御史弹劾户部尚书,言其‘以楮币代银,实剜肉补疮之策’,陛下,前朝覆灭,不无此因啊。”
祝钦云自是从前朝战乱中脱颖而出的平民将军,吃过前朝治国混乱,百姓流离的苦楚,此刻闻言点头,半晌问吏部尚书蓝生道:“蓝爱卿,本朝五品以下官员月俸几何?”
“回陛下,正七品月支俸米七石五斗,折银不足五两,若再行折俸,恐基层官吏难以为继。”
祝钦云沉吟半晌,忽而道:“人人都道治国为民,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但朕看得清楚,这朝朝代代的根基本不在于民,而在于官。这官中不乏王公贵族,或是土地领主,你们才是朕要顶在头上的债家。”
此言一出,众卿慌忙低头道:“臣不敢。”
祝钦云道:“朕记得去年秋收,太原府报称灾田三成,可豫亲王的庄子却多收了两万石租子。”
如今勋贵已被裁了个遍,豫亲王的幽魂怕都已经凉了。祝钦云道:“王公贵胄占着畿内良田,旧制未除,逼得朝廷在百官俸禄上打主意!”
无人应答。
祝钦云语气稍缓:“听说江南有些缙绅,借着义庄的名义兼并田亩,私设关卡征收商税,连漕运的官船都要纳河捐,这些事,各位大臣可知道?”
严忍冬上前,双手托承一副卷好的舆图:“陛下,安庆、宁波、南昌、吉安四府舆图在此,是否通查庄田文牒,还请陛下示下。”
殿内响起此起彼伏的衣料摩擦声,祝钦云起身道:“从今日起,着户部会同都察院,清查天下勋贵庄田,凡逾制占田者,多余部分收归官仓;商税则一概由府县衙门征收,敢有私设关卡者,按贪墨论处。”
钟辞章、严忍冬二人应道:“是,臣领命。”
祝钦云坐下,对钟辞章道:“俸银可暂减一成,然须全以实物支给——糙米按市价七成折算,棉布每匹作银三钱,绝不许用宝钞。”
又看向江雨杭:“通告翰林院,拟道诏书,着各省提学官考察官吏,凡家中田产超过百顷者,今后,不得充任知府以上官职。”
江雨杭、钟辞章点头称是。
祝钦云道:“朕并非要夺人恒产,只是天下的田赋商税,该是养国之基,而非养肥某家某户的私囊。待西部战事稍定,朕自会与诸位爱卿商议,如何将这折俸的银两分毫不少地补回来。”
群臣叩首谢恩,谢正秋手中的狼毫在起居注上沙沙作响,将那些“减俸一成”的条目工整记录。笔尖悬在“补俸”二字上方时,他忽而想起陶然,计上心头,嘴角不禁一笑。
翰林院公署外,槐树沙沙作响。陶然端坐几案前,蘸了蘸朱砂,在错漏处画了个醒目的圆圈,用小楷添了句批注道:“革除积弊者,必承其重。”
窗外传来靴底碾过青砖的急促声响,他刚要起身查看,值房小吏已抱着黄绫卷宗推门而入:“陶大人,礼部急传,着您即刻草拟《清查庄田诏》。”
他礼貌接过,展开明黄色的御制笺纸,笔尖在“贵戚庄田逾制者收归官仓”处悬停。陶家祖产不在京城,查到不是易事,但倘或用心,倒也不难。父亲入京时便购了良田三百亩,加上祖上在西陲的庄子,百顷之数怕是早就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