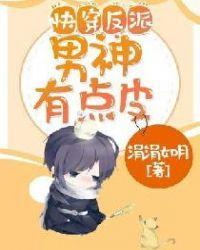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风前絮 > 权力宫斗序章(第1页)
权力宫斗序章(第1页)
“你看看你成个什么样子”,陶父坐着,拿拐杖指着二人,一脸嫌弃,“大庭广众,不顾礼教!你老子娘还在这儿呢!进来问过一句安没有?”
陶然冷笑一声,朝下人问道:“怎么回事?”
无人敢上前回答。
他环视周围一圈,向墨香身后的小厮道:“放开你们的手。”
两人闻言互相看了看,又看了看主座的陶父陶母,见他们并无异议,便悄悄把压着墨香的手挪开。
季眠止住哭泣,挣扎开身后的大人,去替墨香解绳子。
陶然一手揽着静堂,一手朝外唤道:“云生。”
云生进来,他淡然道:“把阿旺拖出去,打死。”
这话惊得在场所有人都为之变色,就连静堂都抬眸看他,表情里掩饰不住得惊惧。
云生愣了半刻,便道:“是!”
说着又唤来了一众小厮,眼瞧着压着阿旺就要去院中用刑。
阿旺挣扎着反抗,皮鞭却又被更多人夺下,只嘴里嚷嚷着:“老爷夫人救我!是这女人的丫头打碎了老爷的瓷瓶,是老爷夫人叫我打的!公子要杀要剐,何必拿我们出气!你去找老爷夫人讨说法去!”
那边,陶父陶母都站起来,气得跺脚,朝下人吼道:“还不快住手!”
一起子小厮有些犹豫,陶然冷声道:“今后这个家谁做主,你们最好心里有数。今日拦一个,我便打死一个,你们尽管听人使唤。”
小厮们互相看看,云生吼道:“还不快去!”
那一起子人便像即刻做了决定,不由分说地压着阿旺就往院子里拖,院子那边,早有人备好了条凳、麻绳和红木粗杖,列队排好要打了。
阿旺像条案板上的活鱼,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静堂摇着陶然的胳膊,阻止道:“你刚刚上任,这话传出去会叫人怎么说?还不快住手!”
他却把她的头轻轻扣下,柔声道:“我有分寸。”
那边季眠已解开了墨香身上的绳子,她把口中棉布一吐,跑到陶然身边道:“陶公子,那汝窑天青瓶我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是夫人她自己打翻的!”
陶然点头,道:“你受委屈了”。又叫人取来椅子给二人坐下,自己揽着静堂站定一旁,看那阿旺已被粗麻绳绑上条凳,木杖一下下落在他的下身。
他疼得鬼叫,嘴里再没力气喊那些不干不净的话,只有哇哇哇的声音,随着木杖落下的快慢转变,不消一会儿,那麻衣上便被血染了深深的一片。
云生悄悄对执杖的小厮道:“手上有点儿分寸,别打实了!”
两人应下,果真打得轻了些,但方才到底是真打得皮开肉绽,此刻轻轻一碰也疼得不可自持,外人听来,依旧是哇哇哇的叫唤。
静堂不忍再看,阳光下,气弱得几近昏倒,一个踉跄往陶然那边跌去。
他慌忙揽住她,听她在怀中喘息着道:“你说过,要和我一起做新的人,就是这样做的吗?”
静堂不可自持地漫出眼泪,陶然闻言心酸,边用指腹抹去,边朝院里道:“住手!”
那边落棒的声音停住,陶然忍了忍自己眼中的泪意,对周围人道:“从今天开始,陶府不再是没名没分的商宅,而是朝廷六品宅第。你们做事,为人都要涨齐眼色,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事能做,什么事做不得。”
“是,”满院侍女小厮跪了一地,低头颤声。
陶然继续道:“我治下的宅子,自是不会蛮横不讲理,但也休要以为我是个性软的,不敢处置了你们。从今天开始,若再有人欺侮颜姑娘半分,对颜家人不敬,阿旺便是你们的下场。”
“是,”一堆人声音更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