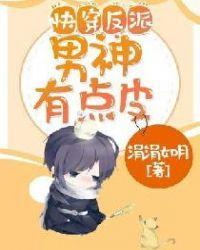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铸金笼 > 6070(第5页)
6070(第5页)
柳惜瑶倒了盏茶给宋澜,问道:“表兄,我听三娘说,如今京中局势已然平稳,你我的婚期可还会再延?”
原以为京中会乱上一阵,两人婚期自是要朝后推,没想到只短短几日便已安稳,如此自不必再推。
宋澜端起茶盏,一饮而下后,那茶盏还未彻底落在桌上,便俯身就寻去她颊边,“表妹心急了?”
粗重的呼吸带来一阵痒意,那圆圆的杏眼瞬间眯起,脸颊与耳珠也倏然升温,变成了那诱人的绯红。
“是、是表兄……成日与我这般,我忧心……”
柳惜瑶话音未落,宋澜便从后掐住那细腰,将她直接拉至怀中,“有何忧心?怕我负你不成?”
柳惜瑶知道,宋澜已是将他能做的全部做了,她不该对他有疑才是,可她也不知为何,心底始终惴惴。
可她也知不能与宋澜说得这样直白,他一腔热忱都给了她,若她还有疑,定会叫他心寒。
“表兄怎会负我?”柳惜瑶软着语调,满眼皆是羞赧地垂了眼尾,也不知是扫了他身前,还是扫了那下处,总归只一眼,她便立即别过脸去,那面容也随之更为滚烫。
“是、是……是忧心表兄的……”
宋澜见她好似已是羞到难以启齿的地步,那微眯的凤眸一怔,倏地一下反应过来。
两人如今住得极近,他但凡得空便会寻来,而寻来后又要与她亲昵,有时只是稍稍耳鬓厮磨片刻,那处就会有所反应,然他不得她点头,又不会当真行至那一步,便只叫自己忍着,忍到口干舌燥,心中发闷,说起话来都哑了声。
原她不是不知,且还为此忧心。
“是忧心我身子?”宋澜抬手将她的脸慢慢转了回来,他喜欢与她说话时,让她看着他。
然柳惜瑶已是羞到一双眼睛不知该看向何处,只能朝那石桌丝上看,用那极轻的声音“嗯”了一声。
宋澜忽地笑了,不管她到底为何忧心,既是她忧心,那他帮她将心结解了便是。
“二月初三,定要你做我宋澜之妻。”
宋澜说罢,合眼将她正要说出口的声音,堵在了唇间。
还有五日便至婚期,迎亲事宜全已布置妥当。
可就一月这最
后一日,京中再次传出消息。
太子于狱中自尽。
依照大盛律令,储君薨逝,百官齐衰三月,京中七日内不得宴乐、嫁娶。
然太子谋逆在先,定罪诏书尚未拟完,他便先一步畏罪自尽,从名义上来看,他仍是储君,可若让其按照储君之礼下葬,皇帝定然不允。
翌日,圣旨传入礼部,皇帝到底还是留了几分余地,念及父子一场,辍朝一日,然太子身负重罪,不得葬入皇陵,只以国公之礼下葬。太子贪饷灾银,愧对百姓,百姓无需服丧。
此讯传入勇毅侯府时,已是二月初二。
便是勇毅侯府不在上京,阖家也并无京官,可到底也是皇亲国戚,连皇帝都顾及父子之情,辍朝了一日,宋家定然也要避讳,别说从简,连那红烛都点不得了。
“怎么也等到三月在办。”
荣华县主开了口,柳惜瑶乖顺地点头应是,坐在一旁的宋澜,却是迟迟不语。
柳惜瑶知道宋澜重诺,但事已至此,她只能认了,又在心底宽慰自己,婚事没有取缔,只是推后一月而已,她要稳住心神才是。
然她表面似极为顺从,没有任何不悦,但那落在身侧的手,却是攥得极紧。
久未言语的宋澜,慢慢将视线收回,抬眼朝荣华县主看去。
“先入族谱。”
他声音微沉,却是字字清晰。
可即便如此,还是叫荣华县主愣了一下,“你说什么?”
宋澜看着她,眸光坚定,一字一句又道一遍,“母亲,儿是说,先让瑶娘入我宋氏族谱。”
此话一出,屋内瞬时又静。
柳惜瑶心头猛地一跳,不可置信地朝宋澜看去。
那上首而坐的荣华县主,缓了片刻后,才又开口道:“礼数尚未齐全,哪里就能先入族谱了?”
柳惜瑶虽是心中触动,但也深知县主所言极是,她不该也不能应允此事,然不等她开口,宋澜便先与她低声道:“你先回朝霞院,晚些我去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