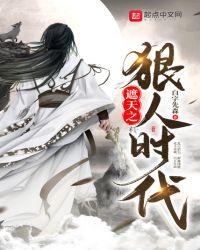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近臣 > 完全是人(第3页)
完全是人(第3页)
焕游笙随公主步入暖阁,目光扫过周遭变化,最终定格在她难掩疲惫却竭力维持平静的脸上。
二人落座,炭盆散发着融融热气。
焕游笙的声音比平日更低沉几分:“公主,我是来告别的。”
世安公主的嗓音带着明显的沙哑与倦怠:“焕姐姐也要走了……听说兰枝昨日也已请辞。”
她抬起眼,目光如易碎的琉璃,带着脆弱的探寻:“焕姐姐要走,是对我失望了吗?还是……对这朝堂的一切,彻底寒了心?”
焕游笙的心被那脆弱刺了一下,她刻意放缓语速,回视的目光温柔而坚定地迎向世安公主:“没有失望,恰恰相反,”她由衷肯定,“我为你骄傲。”
她清晰地看到公主因这句话而轻颤的睫羽。
“这一路走来,你做出的每一个抉择,扛起的每一份重担,我都了然于心。”她的语气转为一种深沉的释然,“只是,我终于看清了,权力于我而言,终究不是归属。”
焕游笙的指尖无意识地划过袖中的圆月弯刀,她回忆起从前在暗卫营时时常萦绕在鼻尖的鲜血气息,忽然觉得那甜腥和权力十分相似:“无论世人如何殚精竭虑,如何心怀理想,历史总在重蹈覆辙,世事永远难求尽善尽美。”
“如今,我接受了这份不完美。也许某一天,时候到了,水滴石穿,乾坤再造也未可知。但公主,我该尽的力,已尽于此。接下来的路,当由继往开来者承接了。”
世安公主身体微微前倾,追问道:“所以,焕姐姐是……看开了?”
她的语气里带着困惑,也带着期盼。
焕游笙唇边泛起一个极淡却真实的笑意:“差不多,但不尽然。世人言‘看开’,总带着几分超然物外的神性,仿佛站在云端俯视众生悲喜。但我不是,”她笑容里带着尘埃落定后的安然,“我只是终于真正地、踏踏实实地,成为了一个‘人’。有血有肉,会力竭,也怀揣憧憬,一个想为自己活一次的凡人。”
世安公主凝视着焕游笙双眸中那湖水般沉静的深潭,这让她微微松弛下来。
她低声道:“焕姐姐,这是你的选择。早在很多年前某个寒风呼啸的冬日,在长安大明宫结满冰花的六角避风亭里,我便已下定决心,会支持你所有的选择。这次也不例外。”
她深吸一口气,汲取勇气:“只是,有些话,我想说与你听。焕姐姐就当是陪我最后一次,好不好?”
“好。”焕游笙专注地望着她,仿佛在无声地说:我在听,我会一直听下去。
世安公主得到这份应允,滞涩的情绪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她目光投向虚空,声音缓慢而悠远,每个字都似从记忆的深渊艰难掘出“母亲……她自登基以来,功勋卓著。设凤阁,革旧俗;破门阀锢蔽,鼎新科举;厉行法治,倡‘以德治国’,一时朝堂之上,君子盈庭;编纂农书劝课农桑,移民关中,广修水利,薄赋轻徭,民生稍苏;丝路驼铃再震寰宇;三教兼容,《三教珠英》集百家大成;诗书风流、太学育人,更开女子教育之先河;北拒突厥、契丹如磐石,安西四镇固若金汤;遣使四方,吐蕃、新罗咸服,边烽不起……可称‘千古一帝’。”
她顿了顿,眼中的光芒黯淡下去:“然而……直至凉州道上,烟尘蔽日,饿殍偶现于道旁,我才惊觉,她设铜匦密告,纵酷吏横行,罗织构陷成狱,使‘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她屠戮汤启宗室近支,仅当年汤雪兰一案后,数千人头顷刻落地,血腥冲天;后来,她更宠信佞幸,纵容面首乱政,为市恩滥赏官爵,终酿明堂之祸;更有甚者,她沉迷神佛,广建寺塔,靡费无度,寺院侵占良田无数……”
世安公主闭上眼睛,仿佛不堪重负:“那时,我痛心疾首,只道她是老了,昏聩了,猜忌专权……”
她的声音哽咽了一下,再睁开眼时,已是泪光盈然,带着深深的自责与彻悟:“自从母亲登基,我便满腹怨尤,不解她何以偏执至此,事事皆欲掌控。可直到如今,直到她……永诀于我,我才真正明白,当初那个自以为清醒、以为能在关键时刻拨乱反正的自己,是多么幼稚可笑。”
“所谓覆水难收,积重难返……身处至尊之位,一念既动,纵使初衷至善,其后诸事亦可如脱缰野马,终将奔向难以预料的深渊。母亲半是神祇,半是妖魔,完全是人。而我,焕姐姐,我也一样。我的‘大义’,我的‘仁善’,我的每一步抉择,最终也……亲手将她推向了末路。”
最后一句,轻如蚊蚋,却字字泣血。
焕游笙始终静默倾听,此刻才出声纠正:“先帝是甘愿赴死。她的选择,是为了你,为了大启江山能平稳交托。那不是你的错。”
“我知道……”世安公主颔首,“我知道她是自愿的……”
可这份“知道”并不能完全消解那份沉重的愧疚。
小剧场:
世安公主:铁骨红梅为什么开了?
焕游笙:它想开了。
![令使很好,所以归巡猎了[星铁]](/img/14858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