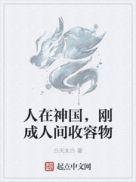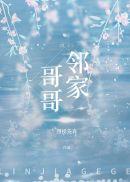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安史之乱:我为大唐改命 > 第759章 气势磅礴的李太白(第6页)
第759章 气势磅礴的李太白(第6页)
王维则神色沉静如水,缓步而行,但紧握的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透露出他内心的凝重如山与不可动摇的决心。他知道,自己手中的笔,即将蘸满的不是墨,而是血与火。
殿外,寒风卷起细碎的雪沫,如同无数冰冷的飞蛾,猛烈地拍打着朱红的宫墙,发出沙沙的声响,更添肃杀。
一场即将席卷天下的有形风暴中心,已然在这宫阙深处铸成。
而另一场以笔墨为刀锋、以人心为战场、更凶险诡谲的无形战役,也在这雪沫纷飞中,悄然拉开了它沉重的帷幕。
接下来的数日,紫宸殿偏殿旁的一间狭小静室,成了帝国风暴的漩涡中心。
窗外,长安城笼罩在战后的疲惫与巨大的不安中,铅灰色的天空低垂,仿佛随时会塌陷。
前夜的冷雨在殿宇的飞檐翘角上凝结成冰凌,此刻正缓慢融化,冰水滴落在殿外冰冷的青石板上,发出单调、清晰而催命的“嗒…嗒…”声,每一声都敲在静室内众人的心坎上,提醒着时间的流逝与任务的紧迫。
殿内灯火通明,数盏牛油巨烛奋力燃烧,发出滋滋的声响,却依然驱不散角落浓重的阴影。
这间临时辟出的斗室,空气凝重得如同浸透了水的棉絮,几乎能拧出墨汁来。浓烈的檀香混合着墨汁的涩味、陈旧纸张的霉味,以及一丝若有若无的、从宫人身上传来的熏衣香,形成一种奇特的、令人神经紧绷的气息。
堆积如山的卷宗散落在案几、地面,各种版本的檄文草稿、废弃的宣纸团如同战后的残骸,无声地诉说着这里正在进行一场何等激烈、耗尽心神的鏖战。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以及窗外那该死的滴水声。
王维端坐于紫檀木案之后,背脊挺直如雪中青松,纹丝不动,仿佛一尊沉静温润却又无比坚硬的玉雕。
跳跃的烛火在他清癯而专注的脸上投下明暗不定的光影,映照出他眼底深处压抑的疲惫和一种近乎殉道者的执着。
他面前摊开的雪浪纸上,墨迹淋漓,字字如刀,散发着凛冽刺骨的寒意。
王维正沉浸于字斟句酌的严谨之中。
他以史家之笔,条陈李璘和李玢“十大罪”,每一笔落下都似有千钧:
罪一:勾结叛逆(七宗五姓为首的门阀),意图分裂社稷……笔锋凝重,引述安史之乱祸源,直指其核心阴谋。
罪二:矫诏自立,僭越称尊,视神器如玩物……笔迹透出冷峻的不屑,引用前朝篡逆典故。
罪三:屠戮宗室,残害手足,血染宫闱……笔触微颤,巧妙地将李璘、李玢指责裴徽杀害宗室的帽子反扣回去,暗示他们是为掩盖勾结叛逆真相而灭口忠良。
罪四:横征暴敛,竭泽而渔,祸乱江南、荼毒蜀地,民不聊生……列举具体苛捐杂税名目,字里行间透出对黎民苦难的沉痛。
罪五:纵容豺狼(蒙骞部),勾结外寇(吐蕃),借搜捕之名行劫掠之实,戕害百姓,人神共愤……直指永王与蒙骞部,杨国忠与吐蕃的勾连,笔锋如鞭。
罪六:阻塞漕运,断绝蜀道,困锁王师,断绝天下生民之望……分析其战略封锁的恶毒用心。
罪七:信用奸佞(七宗五姓),排斥忠良,致使朝纲混乱,贤路闭塞……点名门阀,切中时弊。
罪八:私造战具,囤积粮秣,暗藏甲兵,图谋不轨之心昭然若揭……引用地方密报,坐实其备战事实。
罪九:离间君臣,构陷忠良(指其檄文污蔑裴徽为弑君篡位),颠倒黑白,惑乱天下视听……针锋相对,反击其舆论战。
罪十:悖逆天命,人神共愤!此獠不诛,天道何存?!……最终定论,气势磅礴。
他刚刚落下“罪十:悖逆天命,人神共愤!”的最后一笔,指尖因长时间紧握笔杆而微微泛白,甚至沾染了洗不净的墨色,指甲边缘已有些许磨损。
每一次罪状的书写,都像在他心头刻下一道深痕。
他并非嗜血好杀之人,骨子里浸润着佛家的悲悯与诗人的雅致,甚至本能地厌恶这等赤裸裸的攻讦与构陷。
但作为被新帝委以重任的近臣,作为深知文字力量的史官,他更清楚此刻帝国需要的不是王维的风花雪月,而是足以钉死对手、凝聚涣散人心的铁证如山!
他必须用最严谨冷酷的史笔,构筑起这道关乎新朝生死存亡的正统壁垒。
笔下的每一个典故,都像一块冰冷沉重的砖石,垒砌着新朝的根基,也垒砌着叛逆者的坟墓。
一股沉重的疲惫感如冰冷的潮水般不断涌来,几乎要将他淹没,但一股更冰冷、更坚硬的责任感支撑着他,让他握笔的手稳如磐石,眼神锐利如初。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
“吱呀——”
门轴发出一声压抑的轻响,打破了室内的沉寂,也搅动了凝重的空气。
元载如同一条无声滑入阴影的毒蛇,悄然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