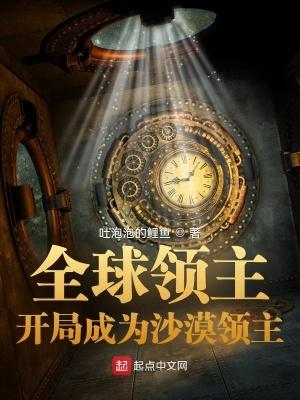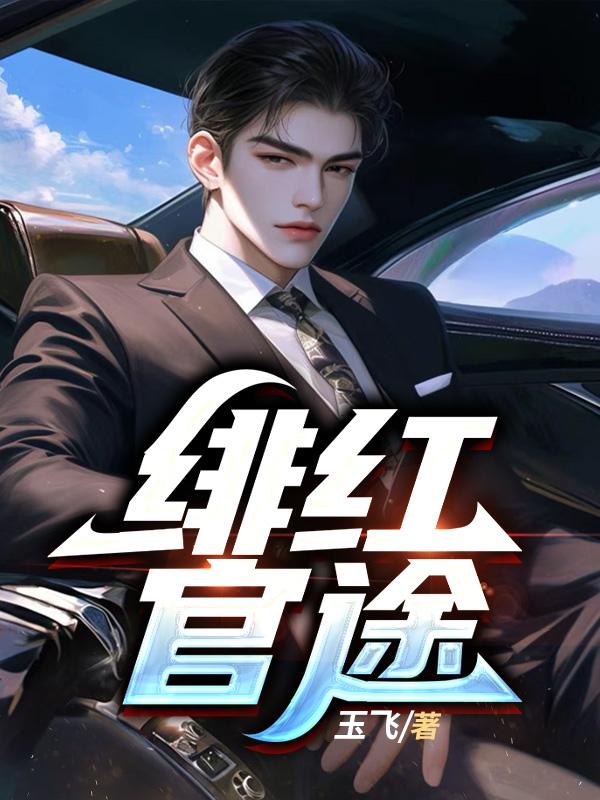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官婿美人香 > 第637章 补救(第1页)
第637章 补救(第1页)
“知道了。”那个声音终于响起,语气平淡,听不出喜怒,“沈静姝这个人,公事公办,原则性很强。你那边,底子干净吗?”
郑国涛额头渗出冷汗,语气急切地辩解道:“市长,您是知道的,开发区盘子大,难免有些……历史遗留问题,有些账目时间久远,经办人变动,可能……可能衔接上有点模糊。但大的原则问题,绝对没有!”
“模糊?”电话那头的声音冷了几分,“国涛,这种时候,‘模糊’就是最大的问题!审计组不是来旅游的!尤其是沈静姝,他眼里揉不得沙子!”声音顿了顿,带着一丝警告,“现在市里的情况你也清楚,向南为什么会到颍阳?这是华志国的一步狠棋。张为民那个人……向来是油盐不进。你记住,屁股要擦干净!该补的手续,该清的账目,立刻!马上!所有动作,都要在规则框架内!别给我,也别给任何人,留尾巴!明白吗?”
“明白!明白!”郑国涛连声应道,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市长的话,与其说是指导,不如说是严厉的警告和划下的底线——市里层面,能提供的庇护极其有限,甚至自身也处于微妙平衡之中,绝不会为了他郑国涛去硬碰硬。他必须自己解决麻烦,而且必须“干净”地解决。
挂了电话,郑国涛瘫坐在宽大的皮椅里,巨大的无力感和恐慌感如同冰冷的潮水将他淹没。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精心构筑多年的权力堡垒,在更高层面的意志和规则面前,竟是如此脆弱。向南这一手,不仅打在了他的七寸上,更是巧妙地利用了市里明争暗斗、强调规矩纪律的大气候,让他投鼠忌器,连在市里寻求强力庇护的路都被堵死了。
他抓起桌上的电话,声音嘶哑地低吼:“让王强和李斌马上到我这里来!立刻!马上!”
一场围绕着“清理”和“补救”的紧急行动在暗流中疯狂展开。郑国涛的核心圈层像被捅了窝的马蜂,彻夜不休。账本被重新翻出,凭证被反复核对,一些模糊不清的支出项目被紧急“完善”手续,一些年代久远的合同被重新“解读”和“规范”。开发区几个重点项目的档案室灯火通明,相关人员被反复“谈话”,统一口径。空气中弥漫着纸张翻动、键盘敲击和压低的、焦灼的交谈声,以及一种近乎绝望的、试图弥补缝隙的徒劳感。
与此同时,向南的办公室却呈现出一种异样的平静。他不再过多关。注审计组的具体进展——他信任沈静姝的专业和操守。他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两条线上。
一条是明线:柳树巷的管网改造试点工程。他顶着“政绩工程”的骂名,反而加大了关。注力度,亲自去现场协调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非人为制造的真正难题,要求务必保证质量和进度。他在一次视察中,当着郑国涛和众多媒体的面,走进低矮潮湿的棚户区,握着一位因常年污水倒灌而苦不堪言的老大娘的手,诚恳地说:“老人家,工程吵到您了,我代表县委县政府给您道歉。但请您再忍一忍,我们一定把这地下的‘病根’彻底治好,让您和街坊们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这一幕被县电视台反复播放,网络上的质疑声浪中,开始夹杂着一些不同的声音。
另一条是暗线:市里。他利用自己并不算深厚但关键的人脉,尤其是市。委书记华志国,谨慎地传递着信息。他从不直接告状,也不渲染问题,只是客观地汇报颍阳县在推进重点民生工程中遇到的、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资金调配结构性困难”,以及县委为了彻底厘清情况、消除隐患、保障发展而主动申请上级审计介入的“积极作为”。这些信息,都被送到了对“规矩”和“风险防控”极其看重的华志国的案头。这些信息,如同无声的砝码,稳稳地加在了支持审计组彻查的托盘上,让市里某些可能存在的、对郑国涛抱有同情或利益关联的声音,也悄然噤声。
审计组的调查如同精密的手术刀,在颍阳开发区的肌体上冷静地切割。一些看似“手续完备”的项目,被抽丝剥茧地发现存在违规超拨资金、土地出让金未及时足额入库、变相返还等问题;一些早已“结项”的工程,其实际投入和产出效益存在巨大水分;更有甚者,发现了几笔流向特定关联企业的“咨询服务费”、“规划设计费”,金额不大,但指向性极其明显。开发区主任李斌被频繁叫去问话,脸色一天比一天灰败。财政局长王强则成了惊弓之鸟,审计组任何一个电话都能让他心惊肉跳。
风暴的中心,郑国涛肉眼可见地憔悴了下去。他眼窝深陷,头发失去了往日的光泽,梳得再整齐也掩盖不住那份心力交瘁。他试图在公开场合维持县长的威严,但那份强装的镇定,在沈静姝审计组那不动声色的专业目光和日益收紧的调查网面前,显得愈发苍白无力。他感觉自己像一只落入蛛网的飞蛾,越是挣扎,缠绕的丝线便越紧。
一个飘着冰冷冬雨的深夜。向南办公室的灯依然亮着。
桌面上摊开的,是审计组刚刚提交的一份初步情况通报。通报措辞严谨克制,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问题指向和证据链的扎实程度,足以让任何知情者心惊。
向南的目光落在通报结尾处,那里列出了几个关键责任人的名字,其中“郑国涛”三个字被圈定在“对相关重大决策负有领导责任,对资金使用监管存在明显疏失”的表述之后。
窗外,寒风裹挟着冰冷的雨点,猛烈地敲打着玻璃窗,发出密集而急促的声响,如同千军万马在奔腾咆哮。颍阳的冬夜,寒冷刺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