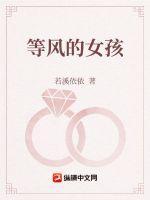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她是金主 > 第91章(第103页)
第91章(第103页)
严家穆赶紧给她拽了过来,啧了一声,“你穿得烂菜叶似的上哪儿去?昨天没洗我忍你一回,现在赶紧洗澡去。”
晏嘉禾表情不悦,仍旧没开尊口,抬手扯开他还要走。
两人挨得极近,一错身间,严家穆除了在她身上闻到酒味和烟味,还有一种奇异的酸腐气息。
这绝不是因为一晚上没有洗澡,而是另一种东西的独特味道。
严家穆明白过来,瞳孔骤缩,没有了玩笑的心思。
他对这种味道十分熟悉,那是国外贫民社区的硬通货之一,“白面”燃烧时标志性的酸味。
严家穆浑身发冷,来不及细想,反手紧紧扣住她的肩膀,喝问道:“你没有碰对不对?说话,你到底碰了没有?”
他捏得太紧挣不开,晏嘉禾皱起眉,终于说话了,拖着燕京的长音,“这打哪儿冒出来的?没毛病吧您?”
“池间叫我来的。”严家穆怕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急急解释,说完又立刻问道:“跟你说话呢,你有没有碰那东西?”
晏嘉禾斜着眼瞅他,出言不逊,“管得着么你。”
像是某种枷锁打开了,又像是加速向下坠去,曾经与人言,句句面上得体,内里暗含机锋,现在全改过去了,阴阳怪气直抒胸臆。
严家穆磨了磨牙,不再扯皮,厉声说道:“把手伸出来。”
晏嘉禾挑起眉嗤了一声,倒要看看他想怎么着,伸了手掌心朝上。
下一秒手上一疼,挨了一条子。
严家穆的鸡毛掸子还没放手,正好掉过头抽在她手心。
“操。”晏嘉禾骂了一句,从小到大还真没人单方面打过她,这下动了真火,收回手在身上摸了摸。
没摸到刀,池间送她的那把蝴|蝶刀,早不知道被她转送给哪个酒吧的少爷了。
这让她陡然一愣。
严家穆趁此机会又把她的手拽回来了,抽了两下,“快点说啊,急死了,那玩意你到底碰没碰?”
掌心有点疼了,晏嘉禾连日酗酒头重脚轻,打架也没力气,还真是被他压着揍。
顾不得管他有什么目的,至少先止住眼前的混乱,“没有,别人吸的。”
对于这些东西,她在犹豫,她用犹豫来延长自己的生命。
严家穆劫后余生似的长舒口气,手一松,连鸡毛掸子都掉到地上了。
啪嗒的声响使他回过神来,又连忙催促着,“赶紧洗澡去。”
晏嘉禾抽回手,左右手互相揉了揉,打量了他一眼,“怪了,我凭什么听你的?你算老几?”
严家穆心里有了底,又恢复了惯常带的三分笑意,算了算本名的笔画,面不改色,“老四。”
“看来严工还不精通本国话,我这可不是问句。”晏嘉禾怔愣片刻后,开了嘲讽,“况且排第四也不是什么好名次。”
“这个名次就是专门管你的。”严家穆针锋相对地回敬她。
还未等晏嘉禾说什么,严家穆知道她果然不会乖乖听话,弯下腰一把把她扛起来,走进厕所,把她扔进放好水的浴缸里。
晏嘉禾扑腾一下,没忍住又骂了一句。
严家穆摁着肩把她压在浴缸边上,胸口以下都在淡红色的加了玫瑰浴盐的水里。
严家穆手速极快地扯过花洒,浇湿了她的头发,从浴缸边的洗发露上按压几下,挤出两大坨液体拍在晏嘉禾的头上揉搓了起来,不多时就起了大量雪白色的泡沫。
他的手法老道,浴缸的边缘正卡着晏嘉禾的脖子,让她像是塞进了断头台,抻着喉咙进退不得。
晏嘉禾反手要挣,察觉到还附带头皮按摩的时候,才舒服得泄了劲,冷哼一声,“严工属实开放,连追人的方法都这么特别。”
早觉着他这人有点古怪,晏嘉禾懒得多问,这样一想就说得通了。
她笑容痞戾,“何必费这个劲,正好我也想开了,人生在世及时行乐,不如咱俩试试?”
严家穆闻言冷笑道:“晏总真是抬爱。不好意思,只是职业病犯了,以前在国外兼职给白人洗宠物狗赚小费。”
他说着动了动脖颈,舒展身手,“尤其擅长阿拉斯加和哈士奇。”
严家穆不待她反抗,拿过上午新买的软毛刷,抵在晏嘉禾的头上快速地刷了起来,细小的泡沫漫天飞舞,飘飘然地落在他的围裙上,墙壁和地面的瓷砖也没能幸免。
“停停,掉头发了。”晏嘉禾觉得头上像来回跑着一台锄草机,连忙伸手按住,“我信了还不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