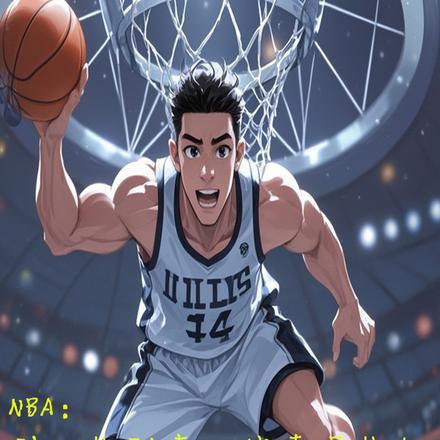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种田文男主拿错反派剧本 > 魔头养成第二百六十三式(第6页)
魔头养成第二百六十三式(第6页)
“……四叔却还耿耿于怀,如此来看他倒不如二叔豁达。”韶言神色微妙。
“人这一
辈子就是这样。”他说,“你四叔生下来就是富贵命,前十几年从没受过委屈,一直顺风顺水。但能有人一辈子走平地不成?”
“可谁晓得他栽的第一个跟头这么大,伤筋动骨不成还要杀人诛心。他这半辈子就这一件不顺心的事,又折磨他二十年。人这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年?他想不通再正常不过。”
“那二叔呢?”
“我……”韶俊平笑了一下,“我没你四叔那么好的命。我从小到大摔得跟头可多了,鼻青脸肿的。这不顺心,那不顺心,不顺心的事情多了,也就不觉得怎么样了。”
“是吗?看不出来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摔出一身淤青,难道还要掀起袖子给别人看?”韶俊平叹气,“咱叔侄二人,中间隔了二十五年。四十年前的事情,我自己都记不太清。过去这么久,什么淤青疤痕洗不去啊?人都死了,我还计较什么!”
“死人应该被原谅。”他喃喃自语,又很快否定,无可奈何地笑起来:“不,不能这么说,是再提“原谅”二字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能拿死人怎么办?学伍子胥开馆鞭尸?还是将其挫骨扬灰?活着的时候拿他没办法,死后折腾出花来又能如何?我倒是想把他挖出来,狠狠扇他耳光,骂“老登你倒是继续和我犟嘴啊,你活着的时候不是挺能说吗”。但他都烂成一团,灰都没了,我想给他一拳
都做不到。”
韶俊平口中的那个“他”是谁呢?
韶言猜不出,也没问。那个人是谁都好,有时候恨只需要一个对象,并不一定非得是具体的。
“不应该原谅死人,棺材又不是免死金牌,怎么就能把他们的孽债一笔勾销。但是韶言,你说怎么着?嘿!你还真就拿死人一点办法也没!好像死是一种最好的逃避方式。咱们只能自欺欺人自我安慰,起码比他们活得长。但是有用吗?活人未必比死人强,有的人死了是一了百了图个清净,有的人活着还是倒霉,一直栽跟头,带着一身的淤青和伤疤进棺材。”
“但只要还有一天可活,就得认真努力地活啊。”韶俊平抬手指天:“起码咱们还活着——先来填饱肚子。”
“倘若活着只为吃饱饭,是不是有些太悲哀了呢?”
“吃饱饭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吗?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读书读多读傻了。”韶俊平拍他的肩膀,“人有时候活得太明白反而不是一件好事,不如稀里糊涂浑浑噩噩一问三不知,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你能说这是错的吗?”
他去扯韶言的脸:“开心点,活着是一件多不容易的事啊,还不珍惜每一天?”
韶俊平的语气没有变化,而韶言眼神放空:“二叔你……”
“二叔都知道。”他说,“你不用害怕,那事轮不到你。”
这笃定的语气竟然让韶言略有心安。
“你的时间还久的很
呢,现在就这么丧,往后可怎么办?”韶俊平深深地叹气,“刀割在你身上,谁也不能替你承受,你只能自己努力习惯,等适应了,就感觉其实还好,没什么能伤得了你。”
“人是只有年轻的时候会这样吗?”韶言问。
“不。”韶俊平摇头,“一直如此。只是适应之后就感受不到刀子割肉的疼,仅仅剩下麻木。”
“但二叔现在也算苦尽甘来。”
“或许吧。”韶俊平挠了挠头顶,“我这把年纪,半截入土的人了,总得过几天好日子。”
今天平静无风,火烧得很稳,韶俊平因此得空和韶言说话。他拿着木棍在地上画圈,一边画一边念叨这是给穗城元英元宗主的,其他的孤魂野鬼可不能抢。
“用不用给元竹也烧点?算了他还有他爹呢……”韶俊平自言自语完,又猛地抬头和韶言说:“你哪天拿几件衣裳来,再找些书本玩具什么的,给元竹烧去。”
他说这话一点也不避人,要是让谁知道他俩在韶氏仙府给元英烧纸钱,指不定又会惹出多大乱子。
韶言无奈:“二叔,这事还是得避着人。”
韶俊平大手一挥:“怕什么,我早就想好理由了。谁要是问起来,我就说这纸钱是烧给你爷爷的。”
“啊?”
怎么无意中元英的辈分还抬高了。
提到父亲,韶俊平难得沉默。他沉思片刻,和韶言说:
“正好提起了。今天是小年,走,一会儿和我去
祠堂你看爷爷奶奶。”
往事随风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