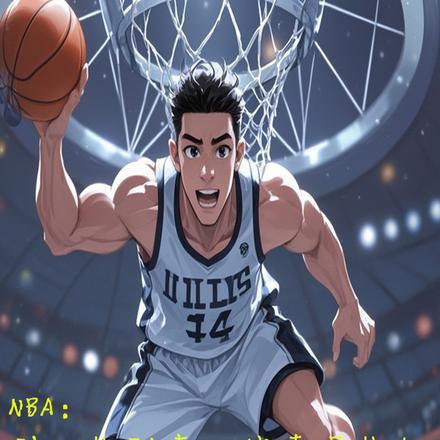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种田文男主拿错反派剧本 > 魔头养成第二百六十式(第2页)
魔头养成第二百六十式(第2页)
“实话实说。”韶言坦然,“我不如他。
”
韶言真心实意这样想。
“但韶氏不是要与池氏亲上加亲……”
“确实是有这个意思,不过我看不能成。”韶言说,“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一方面,可也不能盲婚哑嫁。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还是得两情相悦,男女双方都愿意才好,总不能绑了拜堂!问题就出现在这里,那池氏的小姐我见过的,她的心思不在我兄长身上。人家另有良配,两情相悦,是顶好的姻缘。她眼睛里,是装不下我兄长的。”
“至于我兄长,他对我们那表妹也没什么心思。这桩婚事都不用拆,摆在那里自己就散了。”
韶言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他没什么意思,随意说了些话罢了。韶氏不和池氏结亲,也未必会看得上卞氏。关中郭氏,晋阳李氏……多少双眼睛盯着。但卞氏似乎真的把韶言的话听进去了,动了点别的心思。往后两日,不见卞如彦来,韶言乐得清闲。
卞氏如何想,都和韶言没关系。只是韶言有点可怜那卞氏小姐,她不是被父亲母亲卖到这家,就是卖到那家。韶氏也好,邵氏也罢,都没什么区别。
一个牢笼和另一个牢笼,而她的父母正在为她找一间金碧辉煌的巨大笼子。可那也是笼子。
好像也不能这么说,韶言想,如果她愿意呢,如果真她得到的真是两情相悦的好姻缘呢,是不是就能不那么可悲。
韶言清净了两日,第三日
,那卞氏小姐自己来了。
“你来得正好。”韶言笑了,他刚作好一幅画。卞如英亦擅长绘画,他二人近些日子时常讨论书画。因而韶言见她来,就将新作的画拿给她看。
他个子是真高,大手大脚,在北地男子里也算少见。平心而论,这样一个人是很难有书卷气的。韶言看上去已经算是很文雅了,然而卞如英有时还会觉得他那一双手握笔很奇怪。
“你看上去真不像是会画画的。”卞如英这样想,也这么说了,她知道韶言不会生气。
“是吗?”韶言想了想,笑了:“我可能是像我母亲。”
“令堂也擅绘画?”卞如英惊讶道。
“据说是,而且技艺相当不错。”
“据说”两个字……卞如英心里一紧。
她打听过,知道韶言的经历,也知道他与母亲并不能说是很亲近。但看韶言的样子,他好像也不是很在意这件事。
卞如英道:“如此,我倒是希望日后有机会能和韶夫人探讨一二。”
韶言微微眯起眼睛。
“要真那样,我母亲一定会很开心。”他说,“可惜……实在遗憾。”
“为什么可惜?”
卞如英非要问到底。
“你在冀州,她在辽东,很难有机会。”韶言平静道。
“冀州离辽东很近。”
“天下之大,你未必会被困在一处,日后在哪儿还尚未可知。”韶言像是在开玩笑,“卞夫人的娘家在那么远的闽粤之地,你以后或许也去那边呢。”
话说尽了。
卞如英低下头。
韶言慢慢将那副画从她手中抽离。
“我见了卞小姐你,总觉得亲切,就像见了亲姐姐一样。”他慢悠悠地说,“你我相遇,也算是缘分,又如此志趣相投,实在难得。依我看,我们不如义结金兰,我认你做个干姐姐,可行?”
“再请卞宗主和卞夫人做个见证,往后你我再见,就以姐弟相称。”
这显然有点唐突,可又是在最恰当的时候。
卞如英抬起头,她看向韶言,张口闭口没能说出话来。
“是我唐突了?”
“不。”她笑着摇头,“正合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