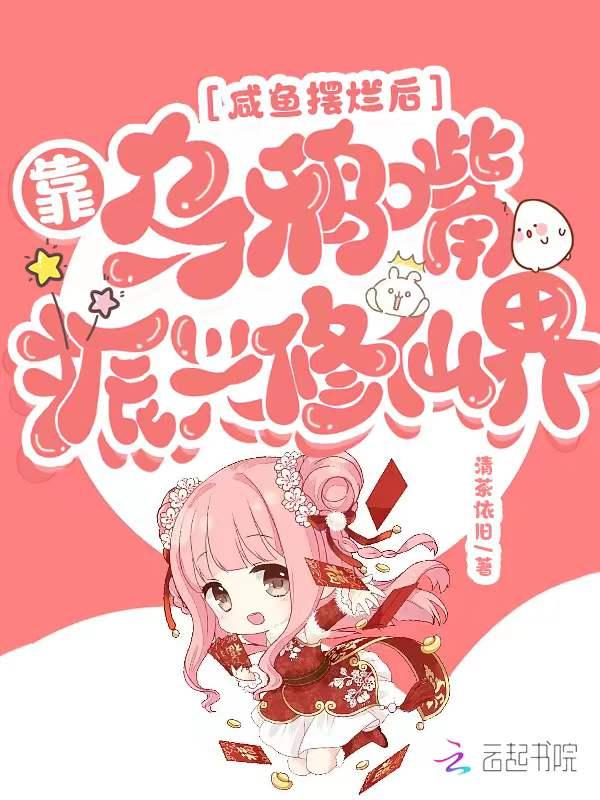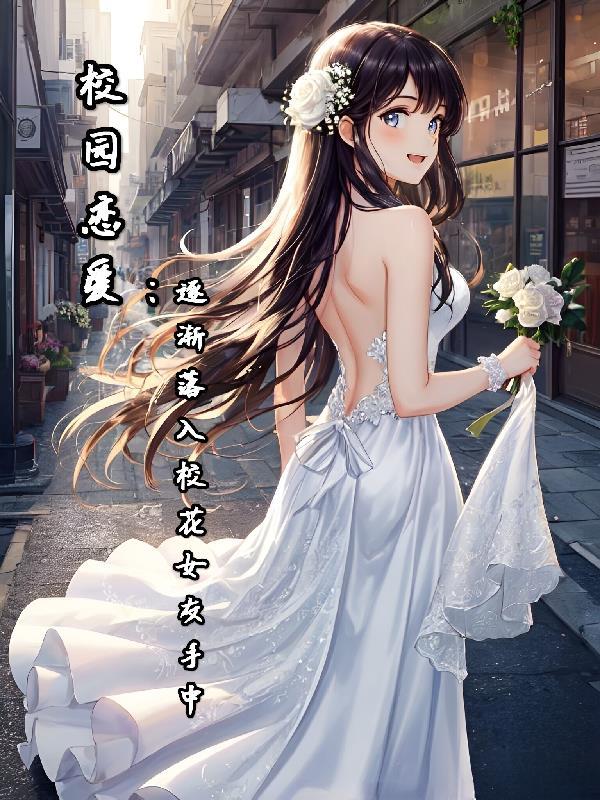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被迫嫁入侯府后 > 第 21 章(第2页)
第 21 章(第2页)
屋子不算大,但有屏风将各处隔开;季松拐了几个弯,方才瞧见了床榻——
床榻上,沈禾双眼紧闭,头发被冷汗粘在苍白的面容上;旁边是弯腰给沈禾擦去冷汗的田田,她弓着腰,听到动静后转过身来,手中的毛巾便被季松给接了过去。
季松拧着眉做完一切,又摸了摸沈禾的额头,确定沈禾没有发热,方才沉着脸又走了出去,目光如炬地望着穗儿:“苗苗怎么了?找过大夫没有?”
“夫人没事,”穗儿低着头轻声道,根本不敢去看季松的脸:“姑娘只是来了葵水,歇歇就好了。”
季松眉头拧得更紧了——
听这话的意思,看来是没请大夫了。
季松有些恼,唤人去请大夫,难得疾言厉色起来:“你从小跟着苗苗,即便做错了些什么,也该是苗苗罚你,我不该插手。”
“可你别忘了,她是我的妻,是宁远侯府的少夫人。她要是出个差池,底下人逃不了干系!”
“是,苗苗为人宽厚低调,不愿意给人找麻烦;我也知道她顾忌着彼此的身份,病了痛了也忍着不说。”
“可沈穗,我告诉过你,遇事了找李斌去,他要是解决不了自然会去找我。”
“你找他了么?”
沈穗低着头不说话,手指不断地搅着,一副老实认罚的模样。
季松顿时更气了——他为的是解决问题,又不是为了耍主子的威风;沈穗这副模样,下回再出了事情怎么办?
“沈穗,”季松深深吸气,声音尽量温和下来:“你老实告诉我,苗苗葵水多久来一次?”
沈穗惊得抬起头来,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掉出来;季松握了握拳,压低声音又问了一次:“你只管如实禀告,我保证,这件事情只有你我知道。”
季松平日从来不耍主子的威风,可身份之别,沈穗一直都记在心里;这回季松做出了保证,分明就是服了软,让她放心。沈穗松开了手,皱起眉头想了很久,方才轻声道:“夫人体弱,葵水……有时六个月来一次,有时七个月来一次。”
季松惊得僵在原地,回过神来声音越发的低:“她……哪里难受?”
“我怎么做,才能让她好受些?”
同沈穗谈完,大夫也来了。
客客气气地给了大夫赏银,叮嘱他千万保密后,沈穗有眼色地离开,说是给沈禾熬些补气血的汤。
季松疲惫地点了点头,又将田田打发了出去,房间一时寂静下来;季松闭了闭眼,慢慢坐到床沿上,自棉被里拉出沈禾一条胳膊来——
她此时肚子疼,胳膊腿也疼,被子里塞满了汤婆子,热得她出了一身的汗。
季松替她捏着。打熬筋骨,平日里少不得跌伤扭伤,懂一些推拿也是理中之义;何况他爹早年征战留下了不少暗伤隐痛,为了让父亲舒服些,季松也跟着学了几分。
胳膊入手,细的好似轻轻一握就能捏得粉碎。季松来不及心疼,只是望着沈禾表情,一点点调整手下的力度,摸索片刻就拿捏准了力度。
推拿按摩不需要多少心思,季松一面推拿一面想,想着沈穗有心为沈禾遮掩,时间间隔定然是往少了说的。如此说来,她一年能来两次葵水就算不错了。
想着他又抬眼望着沈禾,忽然觉出一股无力感来——
她家世低微,他可以让她夫荣妻贵、可以为沈长生请来冠带;她性子内敛,他可以一点点逗得她放下冷静、套出她的真实想法;独独她这副孱弱的身体,季松有些手足无措——
他确实身强体壮,可这不是能够近朱者赤的东西,即便她与他朝夕相处,身体也难以康健起来。
季松眉头皱起,想着方才大夫的话,心中一点点有了计较。
沈禾昏昏沉沉地睡了小两个时辰才有些清醒。她浑身难受,觉得自己在刀山火海里煎熬,觉得有刀剑刺进自己身体,又被丢进火海中。
她有些想哭,却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好在手臂上的按摩能帮她减少几分痛苦,温热的手掌握着她的手腕,多年如一。
沈禾挣扎着枕在那条胳膊上。她闭着眼,话里带着哭腔:“娘……”
声音有些破碎,季松轻轻摸了摸她的脸,又哄小孩一样轻轻拍她后背:“我在呢,别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