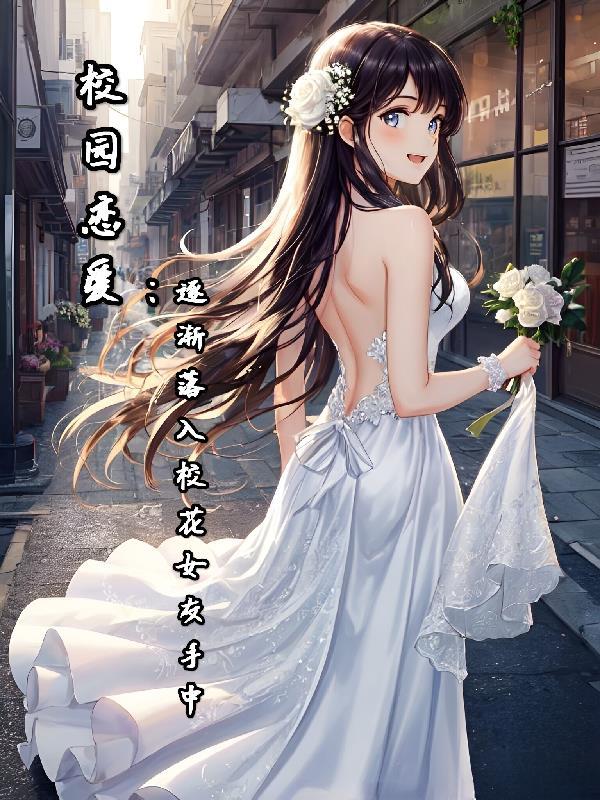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被迫嫁入侯府后 > 六品冠带(第1页)
六品冠带(第1页)
沈禾能看出来自己化用了杜甫的诗,季松并不意外,毕竟李杜诗歌人尽皆知,她又爱读书,肯定没少读过杜甫的诗;可王忠嗣……
她一个闺阁女子,怎么能知道这个人呢?这可是冷门到说书先生都未必知道的人啊,季松也是小时候被父兄押着读书,才知道这个人的。
他夫人那么个弱不禁风的人,居然知道王忠嗣?
季松百思不得其解,却见沈禾坐正了身子。她笑的十分得意:“我有过一位老师,他知道很多东西,于兵法谋略、典章制度无一不知,对朝政时事也很有看法,是个顶顶厉害的人物。”
“哦?”季松更好奇了:“你这位老师是谁?现在还有联系么?我也想拜会拜会他。”
不应该啊,这么厉害的人物,若是哪位大人退休还乡、教几个孩子读书倒也罢了,只当是给自己找个乐子;但怎么会去教一个闺阁女子?
倘若他没有真才实学……也不大可能,沈禾的伯父沈长好毕竟是两榜进士出身,人也做到了鸿胪寺少卿,这职位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人也没少照顾沈禾;倘若她那位老师是个混子,沈禾不该看不出来啊。
季松越想越好奇,沈禾却没有多聊的心思。她叹息道:“早没有联系啦。”
“吴先生只教了我一年,后来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沈禾并不是很想聊这位吴先生;倒不是故意吊季松的胃口、给自己脸上贴金,而是……
而是这位吴先生促成了她和盛羽的婚约。
如今她嫁给了季松,倒也不太好提这件事,便三两句将吴先生带了过去。
“这样啊,”季松倒也没有揪着不放,只惊喜道:“说来,我也有一位了不得的老师。”
“啊?”沈禾一愣,随后笑了:“很正常啊,你是宁远侯的幺子,从小又在国子监里读书,有几位厉害的老师,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是,正是我在国子监读书时候的老师,”季松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苗苗,我老师的六十大寿快到了,你说我该送些什么礼物过去?”
沈禾顿时看向了季松,她慢慢皱起眉头来:“那位老师喜欢什么?性格又怎样?”
“你什么也不说,我怎么知道该送些什么礼物啊?”
季松也笑了。他道:“我那位老师是位大儒,为人清贵有执,堪称清操厉雪,平生唯爱读书一事。”
“那就好说了,”沈禾慢吞吞道:“找他喜欢的书啊,倘若那书太过贵重,你就亲手抄录一份,再装订好了送给他,他肯定喜欢你的这份诚意。”
季松说好:“那苗苗喜欢什么呢?”
沈禾立刻瞪大了眼睛:“不是在说送给老师六十大寿的礼物吗?怎么绕到我身上了?”
季松也瞪大了眼睛。他故作惶恐:“我送我夫人礼物,居然是什么十恶不赦、大逆不道的事情,以至于我的夫人吓成这样?”
季松素来是个强干的人,他想做什么、自然立刻就会去做了;方才与夫人一通闲谈,他越发地喜欢夫人,自然就想着送她礼物了。
“倒也不是,但是……”沈禾哭笑不得:“送人礼物,你怎么可以事先说出来呢?再说了,你应该自己去想送我什么礼物啊。”
季松一琢磨也是这么个理,便点头应了;却还是忍不住问:“苗苗,爹是不是喜欢杜甫啊?”
方才他调侃杜甫,沈禾生了好大的气,一看就知道对杜甫很是崇拜,说不定还有点家学流传。
沈禾说是啊,“爹特别喜欢杜工部,小时候把我抱在膝盖上坐着,一句一句教我背他的诗呢。”
季松了然地点了点头,又见沈禾歪了头问:“你问这个做什么?”
季松讪笑了声:“上回在辽东……我应该是把爹给得罪狠了,这不得好好讨好讨好人家吗?”
沈禾顿时来了兴致:“哦、我们季五公子还记挂着这件事呢?”
这事说起来倒也不难解释,就是当初辽东出了伙劫匪,平日里杀人越货无恶不作,闹到了坐镇辽东的宁远侯面前,他便让自己的小儿子带人灭了他们。
季松应得很干脆,计划做的也很周密——他们在道路上设下埋伏,只等劫匪们抢劫了商人、兴高采烈地抢了货物回去、放松警惕时,他们再杀出去,结果了对方。
但这事必须要有一个诱饵,倒霉的沈家父女就成了这个诱饵。
那时候沈禾站出来陈明利弊,请求劫匪们放过他们一行人,不经意就入了季松的眼。
本来嘛,季松的意思是,商人能保就保,保不了算他们倒霉,到时候褒奖他们一番,就当是感谢他们为剿匪做出的卓越贡献;奈何他看上了人家的闺女,当即改变了策略,假装黑吃黑的劫匪到了两伙人面前,一通黑话说下来,他说要抢了沈禾做压寨夫人,就让自己手下人把沈家人给带走了,自己和那伙劫匪一起讨论分赃的事情。
这事做的很顺利,当天季松他们把劫匪清剿了大半,只剩下些逃出去的臭鱼烂虾,再也翻不出风浪来;做完了事,季松带着那点货物回了家——他让人把沈禾一行人安排在父亲的私宅里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