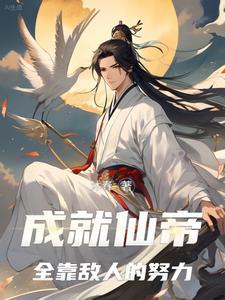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鸣珂 > 第214章(第1页)
第214章(第1页)
他想,自己称帝临朝近二十年,不该是这样的。
皇上躬身摸索着,把桌上堆积的奏折胡乱地拨开,把那张草拟诏书从底下抽了出来,双手发着抖捧着那张纸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惊诧,愤怒与懊悔充斥着他的心胸,却还有着一丝他自己都难以察觉的悲伤与孤独。
他不愿再多想,咬牙切齿地把那诏书撕了个粉碎,一把扔上了天。
他听见有人走进屋来,双手拄在桌上用力地喘着粗气。隔着纷纷扬扬的纸屑,他别过脸见阎止与林泓并肩走进屋来,后者腰间挂着一把宝剑,正警惕地看着他。
皇上一眯眼睛,刚要说话,只听内殿窗外一阵长枪顿地之声,似是卫队换防,整齐肃然。日光明晃晃地落下来,他向四周望去,只见窗外兵甲重重,铁刃冷冰冰地指着殿内,正是傅家亲卫。
皇上哂笑一声,看向阎止道:“傅家的兵,就这么归你了?”
阎止并没有回应他,而是在桌前坐了,提起旁侧的紫砂壶倒了一杯茶放到对面去。壶里的龙井早就冷了,闻不到一丝一毫的茶香,只有浓重的苦涩味。
皇上拄着桌子连动也没动,低头瞄了一下那茶盏,目光却落在林泓腰间的剑上,哼笑了一声道:“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想清楚了,要来杀了朕吗!”
“谋逆之事,臣不会做,”阎止道,“兖州案审理未决,众臣都在前殿等一个示下。近来连日苦热,朝中老臣众多,不宜久站,还望陛下尽早决断。”-
皇上哼了一声,一拂袖慢慢地走回桌后坐下。他对着阎止打量了足足有一炷香的时间,屋里到处都静极了。前殿的喊杀声不知道何时停了,金殿巍巍犹在,只剩下院中远远的蝉鸣声。
皇上顿了顿,又把手肘撑在桌案上,前倾过身,开口时声音里不见发怒,却带着威严与冰冷:“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临徵啊,你远离京城在外漂泊十载,受了委屈,不曾照拂你是朕的疏失。等兖州案一了结,朕会追问瑞王的过失,会重重地罚他。朕也愿意给你亲王之位,和你父亲享同样的食禄——你想要再多些也是可以的。但是衡国公的这桩案子,从今天起到此为止,永不再提!你觉得够了吗?”
“够了吗?”阎止重复了一遍他的话,抬起眼睛看着他,一双眼琉璃珠一样黑白分明,领口的血色一衬显得更透彻了,“陛下问我,敢不敢问一问昔年枉死的冤魂。区区一个亲王位作为筹码,竟然觉得能把这么多亏心事抹平吗?”
“萧临徵,”皇上没有应他的话,只是盯着他,沉声说,“瑞王因兖州这案子见罪于众臣,未来是难再做储君了。朕没有其他的儿子。纵观宗亲之中,适龄又聪颖的只有你。未来这江山,朕甚至可以传给你,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我要这江山做什么,”阎止冰冷的看着他,神色中透着一丝难掩的伤怀,“若非故人扶持,何来陛下今日之位。陛下午夜梦回之时,故人亲朋相问,心中竟没有一丝愧悔吗?”
“住嘴!”皇上霍然而起,居高临下地盯着他,声音里压着喷薄欲出的怒气,“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没有他们,朕坐不稳这个江山吗?朕告诉你,没有他们两个人,朕一样能登位。走到这个位置的功劳全部都在于朕,不在于他人!”
“那你何苦急着杀他?”阎止扶着桌面站起来,今日站得久了,身形轻轻踉跄了一下。
他听见身后剑鞘与腰带轻碰的声音,向林泓一摆手示意自己无事,看向皇上的眼睛时毫不畏惧:“当年北关战败回京,你怨恨他为什么没有死在沙场上。杨淮英纠集十一州上京联告,你查也不查立刻下令让他自裁,连个像样的理由都不肯给出来,又是何等心虚!他一路扶持着你打江山、坐江山,猜疑之下废黜又能如何,为什么一定要要了他的命呢!”
皇上直起身来,忽而厉声:“所有的朝臣都听他的,把朕当成什么了?!你那时候还小,不懂得他究竟位高权重到了什么地步!朕是皇帝,朕才是这个江山的主人,他纠集朝臣、事必躬亲,到底想要干什么!”
“那是因为你实在没有能力当一个好皇帝!”阎止冷冷地看着他,“你对外不通战事,羯人犯边数十年,没有傅家三将,京城早就被踏平了。对内不选良才,一味只听阿谀奉承,又拿着制衡之术沾沾自喜,养出的全是蛀虫和小人。你是他一手选上来的人,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朝局倾覆下去,更不能放任自己的错误愈演愈烈。”
皇上脸色涨红,伸手将桌案上所有的奏折扫到了地上,厉声道:“朕不是!!”
“不是?”阎止不为所动,继续道:“我父亲不想坐这个位子,你是他最敬重的二哥,所以他信任了你。他走了之后,国公爷或许想过当初不应该选择你,但是依然没有辜负故友的嘱托,直到死都是一如既往地辅佐着你,但你又是怎样报答他们的?陛下敢说吗,我父亲是怎么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