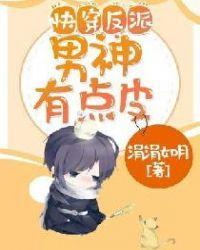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重生1980:从万元户到商业帝国 > 第113章 应声而去(第1页)
第113章 应声而去(第1页)
一个副厂长应声而去,很快拿来一份薄薄的几页纸。赵海接过来只扫了一眼,眉头就皱成了疙瘩。那上面只有几个笼统的,大而化之的数字,什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产品合格率稳中有升”,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种东西,糊弄外行都嫌粗糙。“耿厂长,”赵海推了推眼镜,忍不住开口,“我们想看的是具体的成本核算、设备折旧、库存明细和销售回款记录。”“哎呀,赵总监,你说的这些,太细了。我们厂几万人,几十个车间,那数据堆起来,比山都高。一时半会儿,整理不出来。”耿德生大手一挥,直接把皮球踢了回来,“这样吧,江总远来是客,我先安排人,带你们在厂里转转,熟悉熟悉环境。”这便是赤裸裸的逐客令了。钱斌气得脸都红了,刚要发作,却被江彻用眼神制止了。“好,那就麻烦耿厂长了。”江彻站起身,依旧面带微笑,仿佛丝毫没有感受到对方的敌意。接下来的几天,江彻的团队,就在厂方的“热情”陪同下,开始了“游客式”的参观。他们被带去看的,都是些门面车间。工人们早就得了指示,机器开得震天响,干得热火朝天,一派繁忙景象。但江彻一眼就看出,很多机器都在空转,生产线上磨洋工的人,比比皆是。他们想去仓库看看,被告知“钥匙管理员请病假了”。他们想找车间主任聊聊,得到的回答是“去市里开会了”。整个重机厂,就像一个巨大的、密不透风的铁桶。他们这些外来者,被客气地挡在外面,根本无法触及其核心。晚上回到宾馆,团队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江总,这帮人,根本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钱斌气得一拳砸在桌上,“他们这是在把我们当猴耍!要不,我去找市里,让他们给耿德生施压!”“没用的。”一直沉默的李厂长开口了,他这几天跑遍了几个车间,脸色凝重,“这里的关系,盘根错节。厂领导和市政府,甚至和工人,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从外面施压,只会让他们抱得更紧。”赵海也忧心忡忡:“我们的时间不多,何老那边,只给了我们三个月。如果连基本情况都摸不清,后面的改革,根本无从谈起。”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江彻。江彻正站在窗边,看着远处重机厂那片在夜色中,只亮着零星灯火的巨大轮廓。“既然他们不让我们进去,那我们就把他们,引出来。”江彻转过身,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第二天,一则让整个辽城都为之震动的消息,通过市政府的公告栏、市电视台的滚动字幕,迅速传遍了全城。来自南江省的江氏集团,宣布在辽城设立一个“工业技术创新奖励基金”。公告内容简单粗暴:一、任何辽城重机厂的职工,只要能提出一项有效的技术革新或流程改进方案,一经采纳,最低奖励现金一千元,上不封顶!二、江氏集团下属的“平江精密零件厂”,将在辽城设立分厂,高薪招聘技术工人。重机厂的职工,只要通过技术考核,优先录用,工资待遇,是现在的一倍以上!三、江氏集团将成立“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为所有愿意主动离开重机厂的职工,提供一笔优厚的离岗补偿金,并负责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推荐到南方的合资企业工作。这三条公告,像三颗重磅炸弹,在死水一潭的重机厂,炸出了滔天巨浪。厂里的工人们,彻底炸锅了。“一千块?真的假的?我一个月工资才八十!”“去南方?听说那边遍地是黄金,就是不知道靠不靠谱。”“这姓江的,到底想干啥?这是要挖我们厂的墙角啊!”怀疑、贪婪、希望、恐惧……各种复杂的情绪,在几万名职工心中交织、发酵。耿德生的办公室里,气氛森然。“混账东西!他这是釜底抽薪!”耿德生气得把心爱的紫砂壶都摔了,碎片溅了一地。一个副厂长忧心忡忡地说:“厂长,这招太毒了。他这是绕开了我们,直接跟工人对话。现在厂里人心惶惶,好几个车间的老师傅,都在偷偷琢磨那个什么技术革新了。”“稳住!不能乱!”耿德生到底是经过风浪的人,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他想收买人心,没那么容易!几十年的铁饭碗,是几千块钱能买走的?他这是在破坏我们工人阶级的稳定!”他抓起桌上的红色电话,直接拨通了工会主席的号码。“老徐,发动一下你的人。明天,组织一场‘护厂爱厂’职工大会。就说南方的资本家要来砸我们的饭碗,要让大家提高警惕,不要被蝇头小利蒙蔽了双眼!声势,搞得越大越好!要让市里,让省里,让京城都看看,我们辽城重机厂的工人,不是好欺负的!”,!……江彻的临时办公室,设在辽城宾馆的一个套房里。这几天,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有的是偷偷摸摸来打探消息的工人,有的是想浑水摸鱼的本地小商人。钱斌负责接待,忙得脚不沾地。他学着东北人的豪爽,跟三教九流的人称兄道弟,几顿酒喝下来,倒是套出了不少厂里的小道消息。比如哪个车间主任和哪个副厂长是连襟,哪个仓库保管员在外面倒卖厂里的废料。这天傍晚,钱斌刚送走一个喝得满脸通红的工会干事,就看到三个穿着厚重工装,神情紧张的老工人,在门口探头探脑。“几位师傅,有事?”为首的一个老师傅,犹豫了半天,才从怀里掏出一卷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塞到钱斌手里。“这个……是俺们几个琢磨了好几年的玩意儿。不知道,值不值那一千块钱……”钱斌打开油布,里面是一沓画得密密麻麻的图纸。虽然纸张已经泛黄,但上面的线条和数据,清晰而严谨。他看不懂,但立刻意识到这东西不简单,赶紧拿给了李厂长。李厂长只看了一眼,呼吸就猛地一滞。他一把拉住那几个老师傅,冲进了江彻的办公室,声音都因为激动而变了调:“江总!宝贝!我们挖到真正的宝贝了!”图纸在江彻面前摊开。那是一套,关于大型锻压机液压传动系统的,全新设计方案。“江总,您看这里,”李厂长指着图纸上的一个关键部位,“他们用了一种全新的复合式密封结构,理论上,可以将高压下的能量损耗,降低百分之三十!还有这个伺服控制回路,如果能实现,锻压的精度,能提升一个数量级!”“这套方案,如果能做出来,别说国内了,拿到国际上去,都是顶尖水平!”江彻看着那几个局促不安的老师傅,他们的手上,布满了老茧和油污。“这个方案,你们给厂里看过吗?”江彻温和地问道。为首的老师傅苦笑了一下:“提过,五年前就提过。可厂里的总工程师说,我们这是瞎搞,不符合苏联专家的设计规范。图纸交上去,就石沉大海了。”江-彻沉默了。这就是这个僵化体制最可怕的地方。它不仅扼杀了效率,更扼杀了创新,扼杀了这些最宝贵的人的智慧和热情。“这个方案,我买了。”江彻看着他们,认真地说,“不是一千块。我给你们十万块。并且,我聘请你们,担任新公司的总工程师和首席技术顾问,负责把这台机器,亲手造出来。”十万!三个老师傅,当场就懵了,以为自己听错了,激动得嘴唇都在哆嗦。就在这时,楼下,忽然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喧嚣声。钱斌跑到窗边往下一看,脸色瞬间就变了。“江总,不好了!厂里的人,来闹事了!”只见宾馆楼下的广场上,黑压压地聚集了上千名工人。他们拉着横幅,上面写着“誓死保卫重机厂,赶走南方资本家!”“打倒江彻,还我铁饭碗!”之类的标语。人群情绪激动,高喊着口号。工会主席徐胖子,正拿着一个铁皮喇叭,在人群中声嘶力竭地煽动着。耿德生,正站在不远处一辆轿车旁,抱着胳臂,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他知道,自己赢了。只要闹出群体性事件,惊动了上面,这个姓江的小子,就只能灰溜溜地滚蛋。宾馆的经理满头大汗地跑了上来,声音都带着哭腔:“江总,您看这……要不,您先从后门走?市里已经派人来了,可这阵仗,谁也不敢管啊!”办公室里,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江彻却只是平静地,将那卷珍贵的图纸,小心翼翼地卷好,交到赵海手里。“老赵,收好。这是我们翻盘的本钱。”然后,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风衣,迈步,向门口走去。“江总,您要去哪?!”钱斌急了。“下去。”江彻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他们会打死你的!”江彻回头,看了他一眼,笑了。“放心,工人阶级,不打自己人。”他推开门,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独自一人,走向了楼下那片愤怒的,如同即将喷发火山般的人群。辽城宾馆门前的广场上,群情激愤。上千名工人将大门堵得水泄不通,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工会主席徐胖子站在一个临时搭起的高台上,正用他那被酒精和香烟浸泡得沙哑的嗓子,进行着慷慨激昂的演说。“同志们!工友们!我们身后,是养活了我们祖孙三代的工厂!我们脚下,是共和国工业的长子!现在,有南方的资本家,要来砸我们的锅,抢我们的饭碗!你们说,我们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人群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回应。耿德生站在远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法不责众,这么大的场面,足以让市里、省里,甚至京城的何老,都感到棘手。到时候,为了维稳,牺牲一个外来的“顾问”,是必然的选择。,!就在这时,人群后方,忽然起了一阵骚动。骚动像是涟漪一样,迅速向前扩散。激昂的口号声,渐渐平息了下来。所有人都回过头,看向宾馆的大门方向。只见一个穿着风衣的年轻人,独自一人,从门里走了出来。他没有保镖,没有随从,甚至脸上都没有一丝一毫的紧张。他就那么平静地,一步一步,走下台阶,走到了汹涌的人潮面前。是江彻!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们想过他会报警,会躲起来,会灰溜溜地从后门溜走,却唯独没想过,他敢一个人,赤手空拳地走出来,面对上千名愤怒的工人。这股子出乎意料的胆气,让原本喧嚣的广场,诡异地安静了下来。江彻站定,目光缓缓扫过面前一张张或愤怒,或迷茫,或麻木的脸。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足足一分钟,广场上,落针可闻。只有北风呼啸的声音。这种无声的对峙,比任何激烈的言辞,都更具压迫感。工人们开始感到不安,他们交头接耳,不知道这个年轻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台上的徐胖子也懵了,剧本不是这么演的啊!他清了清嗓子,拿起铁皮喇叭,色厉内荏地喊道:“江彻!你还敢出来!你这个妄图破坏我们国企的资本家,今天,我们工人阶级,就要……”“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江彻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广场上,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你们上一次,准时足额领到工资,是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像一根针,精准地扎进了所有人的心里。人群出现了短暂的骚动,但没人回答。“我再问一个问题,”江彻继续说道,“你们厂里生产的那些大型机床,去年一年,卖出去了几台?是十台,还是五台?”:()重生1980:从万元户到商业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