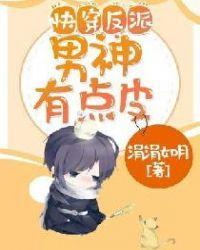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心劫 > 第135章(第1页)
第135章(第1页)
沈今生急促地喘息着,脸色比之前更加苍白,额角渗出细密的冷汗,她挺直了脊背,迎着赵元姝震惊到近乎失态的目光,眼神里没有半分羞怯,只有一种近乎悲壮的决然和如释重负的坦荡。
“殿下看清楚了?江南道乌镇沈家,被灭门时侥幸逃脱的遗孤,非沈家公子,而是……沈家小姐,沈素。”
她微微垂下眼帘,复又抬起,“殿下天人之姿,恩威并重,臣感佩于心。然,臣女身之实,欺瞒在先,已是大罪。更不敢以蒲柳之姿、污浊之身,玷辱殿下清名,行此悖逆人伦、混淆阴阳之事。殿下欲寻知己、觅良配,臣……非良配,亦不敢为殿下之刀于榻上。”
“此前种种,皆为自保求生,不得已而为之。今日坦诚相告,甘领殿下一切责罚。唯望殿下念在臣尚有微末之能,可效犬马之劳于国事,留臣残躯,为云州百姓、为殿下驱策于疆场案牍之间。至于其他……恕臣,万死难从。”
沈今生说完,不再看赵元姝的脸色,将被撕裂的衣襟勉强拢起,遮住那片刺目的真相。
车厢内只剩下她压抑的喘息和赵元姝死一般的沉默。
赵元姝缓缓地、缓缓地收回了僵在半空的手,指尖微微颤抖,她深吸一口气,再开口时,声音恢复了惯有的清越。
“沈素……好一个沈素,本宫……倒是越发看不透你了。”
“今日之事,本宫……记下了。”
沈今生策马返回云州。
暮色四合,城门在她面前缓缓开启。
门洞内灯火通明,映照着守门士兵复杂难辨的眼神——敬畏犹在,却混杂着浓得化不开的困惑、质疑,甚至一丝被背叛的愤怒。
马蹄踏在青石板上,清脆的回响在空旷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刺耳。
街道两旁,闻讯聚集的百姓挤满了视线,与以往领取稀粥时的麻木不同,此刻每一张脸上都交织着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对未知未来的惶恐。
“安抚使大人回来了……”
“朝廷的官了?咱们……咱们算不算从良了?”
“陈将军那边怎么说?能答应吗?”
“听说长公主亲自招安的,还给沈大人封了大官……”
“唉,当官好是好,可那些狗官……”
这些声音钻入沈今生的耳朵,像无数根细针,她挺直了背脊,下颌绷紧,目光平视前方。
府衙前的广场,灯火通明如同白昼。
陈拓高大的身影矗立在石阶的最高处,他并未着甲,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战袍,双臂抱胸,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他身后,是疤狼等核心头领,以及数百名闻讯赶来的赤焰老兵。
疤狼看到沈今生,眼神复杂地动了动,但触及陈拓那山雨欲来的气势,终究没敢上前。
沈今生勒住马,翻身而下,她将缰绳随手递给迎上来的亲兵,脚步沉稳,一步步走向石阶,走向那片沉默却汹涌的怒潮。
广场上死寂一片,落针可闻。
所有目光都聚焦在这两人身上。
“将军。”沈今生在石阶下站定,声音清晰,不高,却足以让前排的人都听见。
陈拓没有回应,只是死死盯着她,胸膛剧烈起伏,半晌,才道:“安抚使……大人?好,好得很!沈兄弟……哦不,沈大人!你这一趟出去,真是给兄弟们挣了个天大的前程啊!朝廷的官帽子,沉不沉?戴得可还舒坦?!”
最后几个字,是吼出来的。
人群一阵骚动,老兵们的呼吸都粗重了几分,眼神中的愤怒几乎要喷薄而出。
沈今生没有躲闪,任由那利剑般的目光刺在身上,声音依旧平稳,“将军,粮车入城,李勣退兵百里,云州之围已解,数万军民,今日可食饱饭,夜里能安枕,不必再枕戈待旦,忧心明日城破人亡。此乃眼前活路。”
陈拓嘴角抽搐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