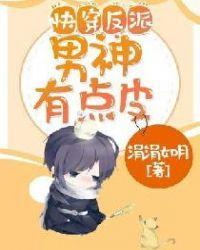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龙傲天前夫想和我破镜重圆 > 18心动六(第3页)
18心动六(第3页)
前几日朝玄修行至夜半,常常黎盏歇下了他还未归,白日比他一个要去上课的还早起,黎盏自然以为他今日也不会在屋内,谁料推开屋门,二人几乎是直勾着撞了个照面。
那盏许久未灭的油灯昏黄,将朝玄的影子拉得很长,映在墙面之上。
他身形端正,靠在案前,平静地翻阅着一本剑谱。
黎盏有些意外:“你在屋里啊。”
朝玄掀起眼睫,看到黎盏衣上沾染的泥沙,连同沾了泥灰的脸颊与披散长发:“受伤了?”
黎盏心不在焉,“啊”了一声:“回来的时候摔了一跤,”他习惯去补全自己的谎话,抱怨张口就来,“有点疼,我睡一觉,休息会就好了。”
“哪摔的?”
“紫极峰和明隐峰相接的栈道,不知道谁练剑的时候把一块山岩砍碎了,我没看路,侧着摔在了地上,后肩都擦伤了。”黎盏继续胡扯。
朝玄放下手中的书:“我看看。”
“什么?不用,其实也没什么,好像已经不疼……”黎盏脸色忽变,一下激灵起来,慌忙推拒,“真的不用……”
屋舍很小,朝玄动作也快,三两步距离,黎盏阻止不及,只得指尖微动,飞快地掐出一道障眼法,为自己随口的扯谎负责。
朝玄:“我只有镇上买的药膏,你有习惯用的吗?”
“……没有,就那个吧,反正不是什么大伤。”
黎盏卷起衣袖,露出被砂石擦伤的小臂,他很久没有受伤,都快忘记正常的伤痕是什么模样。
下手稍微重了一点也是正常的吧?
朝玄看着还在往外淌血的小臂沉默了。
“你摔得……还挺狠的。”
他重新起身,去屋外接了水,取了干净的布,替黎盏将砂石从伤口清理干净,涂抹膏药。
黎盏身上其实并没有真的伤口,药膏涂抹之处丝丝凉凉的。怕不慎弄疼黎盏,朝玄便靠得近了些,握着他手臂的掌心却温热。
黎盏有些不习惯与人这样亲近,低声催促:“好了吧,反正都已经不疼了,实在不行你把药给我,我自己上。”
朝玄直截了当翻过他身子,将衣衫从肩头褪至肘间,露出一截清瘦的后背与两块微凸肩胛,绸缎似的长发垂落,遮住左肩下粼粼点点的伤痕。
他不是没有脑子,自然也明白黎盏在骗自己。
什么摔伤能伤到这个地步?进屋时,也明显没有想到会有第二个人。
纵是日夜相处之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对方不愿意告知,他也没有立场和资格去探求,只是即便知晓这个道理,看到伤痕时,也依旧难免心中空落,怪异地泛出些许滋味来。
朝玄垂下眼,将黎盏长及腰臀的长发单手捧起,置于前胸。屋舍逼仄,烛火摇曳,像是为这层雪腻的肤。肉覆上一层釉色,连带着二人的靠近都生出了些许融融暖意。
他上药一向以高效率著称,力道重了也未觉察,至黎盏轻轻闷哼,方道:“弄疼你了?”
黎盏很久没用与人这样亲近,有些不太自在,他本想去责怪朝玄,微一偏头,对上一双漆黑明亮的眼睛。
……
怎么那么像一个人。
黎盏舌尖抵着上颚,又是烦厌又是忍不住想多见一会这道阔别百年的讨厌表情。
他行事随意顺心,还存着股暗戳戳的焉坏,于是眼睫弧度一弯,略带些欲迎还拒之意,轻飘飘地瞧他又别开,留下一点泛着酡红的眼尾。
朝玄涂药的手停在半空不动了,黎盏心念稍起,顺势往后一靠,半缩着身子,鼻尖埋在他脖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