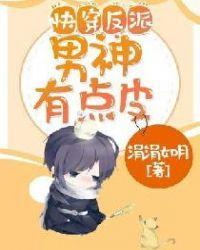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万人嫌受和万人迷攻 > 13他知道那个万人嫌贺宁回来了(第2页)
13他知道那个万人嫌贺宁回来了(第2页)
闻君鹤那日说出他误会贺宁的话时,贺宁看着他,仿佛眼前这张英俊的脸突然腐朽成灰,碎成了一堆骨头。
人人都道闻君鹤清高自持,贺宁在那一刻看透了他骨子里的傲慢与自私,那种根深蒂固的、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肯放下身段问一句真相的冷漠。
所有人都说贺宁骄纵,可真正骄傲到骨子里的分明是闻君鹤。
曾经让贺宁着迷的特质,如今却成了他最仇恨的地方。
原来爱恨就真的在一瞬间。
贺宁坏,也坏得坦坦荡荡,他不需要这种迟来的同情,恶心这种虚伪,更不想再犯贱似的凑上去讨要一点温存!
贺宁对闻君鹤的愧疚像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心口多年。
可闻君鹤何尝不是用几年的冷暴力,一刀刀凌迟报复了回来?
哪怕闻君鹤是块石头,对他没有一点心动,贺宁都不会失望如此,可闻君鹤明明都知道,他也不是对他一点都没有感觉,他就是故意的。
他忽然觉得轻松,那些自欺欺人的期待,终于可以放下了。
他不欠闻君鹤的,也不欠任何人。
这场长达五年的自我折磨,该到此为止了。
周纪看着贺宁穿着一件裁剪得非常流畅的西服,称赞道:“很好看。”
贺宁对他露出一抹微笑,周纪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贺宁身上那股像清晨初阳底下那份拘谨和压抑彻底消失了,变得无影无踪了。
仿佛一直禁锢他的什么心结彻底消失。
“……纪哥,你也很帅。”
周纪拉起贺宁的手,璀璨的灯光下,他抬起眼:“以后叫我阿纪吧。”
“……阿纪。”
周纪看着他:“贺宁,我们都不要后悔。”
白色的玫瑰花瓣洒落,悠扬的音乐响起,露天下像是被翻新过的草坪上是来往的宾客,贺宁靠着他不是很出色的记忆力,记住了周家大大小小的来往亲属身份。
巨大的露天台上,纯白的背景墙,到处都是鲜花和气球,远看像是精修的风景图片。
贺宁站在人群中央,白衬衫的领口熨帖地贴着修长的脖颈,西装裤的剪裁恰到好处地勾勒出笔直的腿线。
阳光透过教堂的彩绘玻璃落在他身上,淡妆修饰过的五官在光影交错间显出几分不真实的精致,整个人像是被镀了一层柔光,他漂亮得像是下一秒就会振翅飞走的天使。
孟轩坐在第三排靠走道的位置,手肘支在扶手上,掌心托着下巴。
他眯起眼睛看着贺宁的侧脸,视线从对方微微扬起的唇角滑到握着捧花的指节,司仪的声音忽远忽近,他想起几年前的另一个午后,贺宁也是这样站在鲜花拱门下,面前的对象是闻君鹤,孟轩记得太清楚了,贺宁踮脚亲吻闻君鹤时那笑容里带着孤注一掷的甜蜜,仿佛要把自己烧成灰烬献祭般的爱。
很刺眼。
现在贺宁的笑容很得体,很标准。
周纪拿起左右手递上来的戒指,然后戴进了贺宁的无名指里。
周纪笑得温柔,贺宁在他脸侧落下一个亲吻,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周牟富和他的夫人坐在台下,听着身边的动静,最终抬起手也跟着拍了两下,嘴角微微扬起形成一个比较满意的弧度。
周牟富想起前几日贺宁来找过自己。
他说:“叔叔,你要对周崇狠不下心,我们这场婚礼办不成,办不成,他会一直纠缠周纪。”
“两个儿子,总得保一个吧,您不能为了个非亲生的,把亲生的不当人。”
婚礼举办的时候,周家走廊尽头的那盏灯始终亮着,保镖像两尊雕塑般立在门外,不敢松懈一刻,仿佛里面关着的不是人,而是一头随时会撕破牢笼的困兽。
房间里传来重物砸向墙壁的闷响,玻璃碎裂的脆声,还有布料被撕扯的刺啦声。床单被扯得半垂到地上,枕头里的羽绒飞散在空气里,飘得像一场不合时宜的雪。
而始作俑者就仰躺在凌乱的床褥间,漆黑的眼珠一眨不眨地盯着天花板。
他猛地弹坐起来,赤脚踩过满地狼藉,瓷器碎片在苍白的脚背上划出细小的血痕,可他像是感觉不到疼,只是疯了一样拍打着厚重的房门,指节在实木上撞出沉闷的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