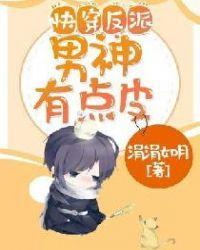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万人嫌受和万人迷攻 > 13他知道那个万人嫌贺宁回来了(第1页)
13他知道那个万人嫌贺宁回来了(第1页)
婚礼当天晴空万里。
贺宁站在穿衣镜前整理领结,小声嘀咕着“上次不是办过了”,周纪从身后经过说:“办几场不是办,我就是要让我的婚事全城的人都知道。”
周家人的态度对贺宁来说用泾渭分明四个字可以形容,表面礼数周全,也仅限于此。
比起虚情假意的热情,贺宁反倒觉得这种直白的疏离更让人安心。因为至少这些轻蔑,声势浩大也不浩大,伤不到他分毫。
他们的婚礼筹备得匆忙,连礼服都来不及定制,只能临时在品牌店挑选。
那日贺宁赶到国外的时候,周纪侧颈上还留着狰狞的吻痕,像是被人狠狠咬出来的。
周崇当时脸色阴鸷地盯着贺宁:“你居然还来这里?”
贺宁平静地反问为什么不能,伸手就要拉周纪离开。
贺宁不知道周崇刚才跟他说了什么,只听见周纪自嘲般低语:“拉你蹚这浑水……我是不是做错了?”
贺宁摇摇头,当所有人都对贺宁的落魄冷眼旁观时,只有周纪愿意朝他伸出手。
所以现在,贺宁心甘情愿陪他演这场戏,用一纸婚约洗刷那些“乱伦”的污名。
反正贺宁早已一无所有,名声、尊严,都随着贺家的倾塌碎成了渣。
“我受不了他这样的爱。”
没有爱该是这副模样,充满算计,扭曲的占有欲,还有那些以爱为名的伤害。
贺宁说:“那就别接受。”
贺宁的手指抚过陈列的西装,忽然想起多年前那时候他也像现在这样,站在试衣镜前整理衣领。只不过当年穿的是纯白礼服,设计师亲手为他别上胸针,店员拉开帘子时布料摩擦发出“唰”的声响。
记忆里的闻君鹤坐在沙发上抬头。贺宁当时紧张得手心冒汗,不停地摆弄袖口的袖口,像个待嫁的新娘似的羞赧不安。
闻君鹤目光在贺宁身上停留了很久,手指无意识地在手机边缘轻敲,屏幕上的新闻页面早就暗了下去。
贺宁被那目光烫得手足无措。他扑到闻君鹤身上,胳膊环住对方的脖子:“到底好不好看?”
声音里带着撒娇的意味,贺宁说:“你别光看着不说话啊。”
闻君鹤被他闹得没办法,淡淡评价了句“太浮夸了”。贺宁立刻撇嘴说他敷衍,搂着闻君鹤说他想要一切都漂漂亮亮。
贺宁兴致勃勃地为闻君鹤挑了套礼服,纯白的燕尾服,袖口绣着繁复的金线,是他最爱的风格,却也是闻君鹤嫌恶的设计。贺闳兴觉得儿子简直在玩过家家的游戏,并不觉得荒谬而叫停。
那时候的贺宁活得像个不知疾苦的小王子,贺闳兴无底线的溺爱给他铸了层金钟罩,让他觉得全世界都该围着自己转。虚假的朋友们捧着他,恋人会一直在他身边,连那些无理取闹的要求都会被一一满足。
后来贺家倒了,贺宁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标好价格”。
去探监时,他换上轻松的表情对贺闳兴说“我过得挺好,我把自己照顾得也很好”。
贺宁对每一个人这样说,他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玻璃那头的贺闳兴日渐苍老,眼神却愈发锐利,他看穿了一切告诉贺宁说:“宁宁,别难过,失去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
贺闳兴当年说闻君鹤不是良配时,是在保护这个被宠坏的儿子,不要尝到求而不得的苦。
贺闳兴给贺宁筑了二十多年的金丝笼,却没教过他该怎么面对笼外的风雨。等保护罩突然碎裂,贺宁像只被扔进狼群的羊羔,跌跌撞撞地应付着陌生的人情世故。那些曾经巴结他的人,看他的眼神像在看路边的垃圾;曾经唾手可得的东西,如今拼尽全力也够不着。
贺宁渐渐学会把自己缩进壳里,像旁观者一样看着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直到闻君鹤前几日说出他多年心结,贺宁才惊觉自己活得有多失败,想要的爱得不到,该有的信任也寥寥无几。
贺宁这些年把自己钉在原地,像赎罪一般不敢靠近,不敢纠缠,只盼着闻君鹤某天回忆起来,能给他一句“还算识趣”的评价。
他总想着,尽管他爸做过那些事,但他们好歹有过几年好时光。
可闻君鹤压根没这么想过。
多讽刺啊,他们在一起四年,不是一年两年,贺宁掏心掏肺地对他好,到头来闻君鹤宁可信外人几句挑拨,也没给过他半分信任。
那个人还是伤害他的人。
那些温存时刻,在闻君鹤眼里大概只是被迫的敷衍,他的真心,在闻君鹤那里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