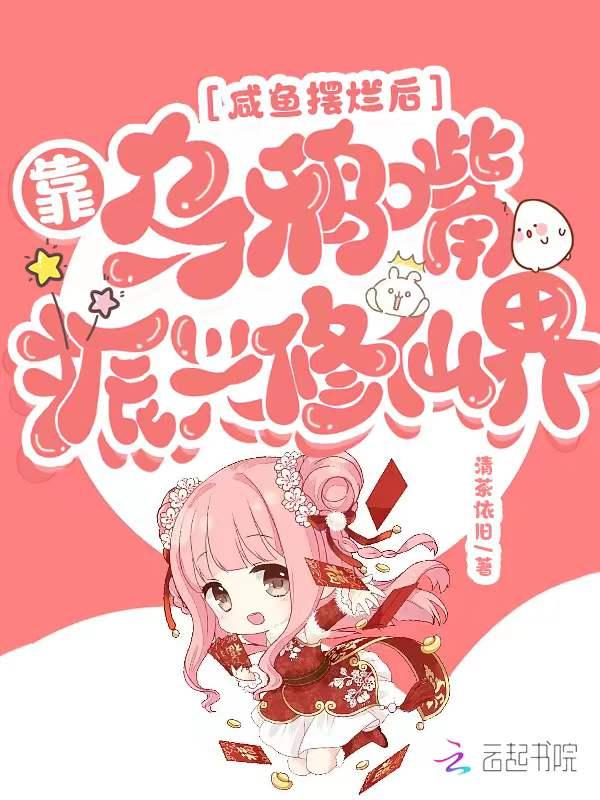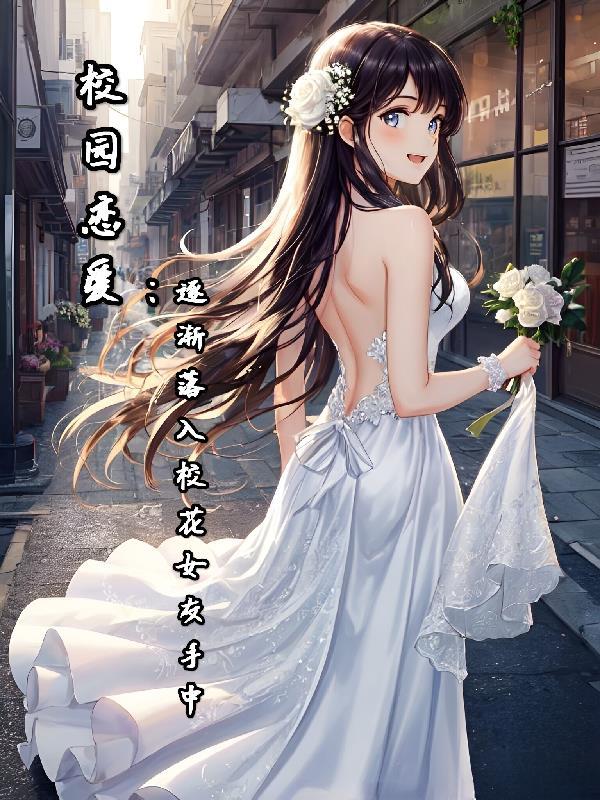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和离后主公他追悔莫及 > 5第 5 章(第1页)
5第 5 章(第1页)
话音刚落,院内一静。
两个人仿佛都被这句话瞬间冻住。
银霜和姜辞脸色同时一变,姜辞更是一时愣在原地,连福身都忘了收回。
她只觉耳畔“嗡”地一声,姬栩也是一怔,眼神在亲儿子与眼前这位未来的弟媳之间流转片刻。
他微微一笑,语气轻柔,带着一点无奈的宠溺:“胡说什么呢。”
“姜姑娘是你二伯未来的夫人,也是你以后的二娘,岂容你胡乱拿来玩笑?”
说着,他伸手摸了摸姬云梵的头,语气温和却极稳,像是要给他讲些道理:“世间婚事,不是你一句娶了吧就能定的。”
“若真有一日你要说这种话,那也得学会先问问人家女子愿不愿意。”
姜辞垂着眼睫,听得这话,心中微动。
她看了看面前这个小孩子,心里忽然有些想笑,又说不清到底是在笑他,还是在笑自己。
只是笑意未显,眼角却泛出一点潮意,谁又问过她是否愿意呢。
她轻轻福身,声音平和而疏淡:
“阿梵童言无忌,大公子莫要怪他。”
姬栩看着她的神色,眼底闪过一丝深意,但终究没有多言,只温声道:
“无妨,也请姑娘勿放在心上。”
“他年纪尚小,话不经意。”
姜辞微笑点头:“我懂。”她与二人告别,带着银霜离开姬栩院中。
一路行来,银霜一语不发,姜辞也未出声,直到走出廊下,风吹得她鬓发微起,她才像是忽然回过神来般,轻声道:
“适才那话……当真让人难堪。”
银霜也松了口气,附和道:“那孩子虽是无心,却叫人措手不及,不过没想到大公子性格到时极好相处,奴婢瞧着比都督好多了。”
姜辞抿唇,没再多言。
回到院中,她换下外袍,坐在榻边,她忽然开口问道:“姬家大公子……得的是什么病?为何病了这么多年,也不见痊愈?”
晚娘正在摆茶,闻言一顿,放下茶盏低声道:
“听府上的人说,具体是什么病也无人能断准。”
“前几年姬夫人确实遍请名医,东阳本地的大夫都来过了,但最后也都摇头离去。”
“说他五脏虚火上行,舌焦口燥,夜不能寐,还常年心悸、气血翻涌……试过温补、试过清热,试过针灸、汤药,皆不见。”
姜辞微蹙眉头:“那为何不请懂毒者来一试?”
晚娘低声一叹:“姑娘说得虽是理,但这世道乱了,许多良医早死,要么找地儿归隐,还有歹人当道,能医者和会医者,本就是两码事。”
“府中也不是没人想到以毒攻毒的法子,可真正能用毒而不伤命者,世间寥寥无几。”
“况且,那位大公子是姬家嫡长,谁敢轻试?”
姜辞微微点头,垂眸思忖。
伏火毒,灼而不烈,沉而不爆,确实不像寻常虚损,若一味温补清凉,只会扰乱经脉。
她目光沉下去。
夜深人静。
案上孤灯如豆,姜辞披着一袭素衣,独坐书案前,窗外风过竹影,烛火微晃。
她提笔蘸墨,铺开信纸,她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