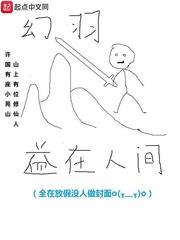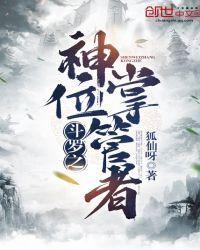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激流[刑侦] > 140146(第5页)
140146(第5页)
站在后排的夏怀瑾和侯万征皱了皱眉,刚想上前,却又止住脚步。路从辜始终站在应泊身后几步的位置,眸色低垂,他牙关紧咬,手攥成了拳都能感到手背上的青筋在跳。
谁都知道,应泊确实需要扶一下了。
但没有一个人动。没人敢去戳破这个平静的泡沫,没人敢接下那一句“对不起”后的沉默。所有人都知道——应泊一旦哭出来,这一场葬礼就不止是送走张继川,而是把这个在风暴里苦苦撑着的人,一并埋进去了。
应泊自己也知道,于是他站直身子,眉目低垂,像压住洪水一样吸了口气,把所有马上冲破眼眶的东西都憋回去。
而后,他回过头,对礼仪人员点头致意,低声说:
“可以开始了。”
告别乐响起的时候,他重新站回了最前排。
阳光照在他的背上,像一张宽阔的墙,光从缝隙里漏下来,直直地洒在墓碑前那一张青年的遗照上——照片里的人,笑得仍旧灿烂如昔。
埋骨仪式结束后,张父沉默良久,最终只说了一句:“他之前跟我说过,他特别佩服你。”
应泊低下头,再没抬起来。
直到所有人都走光,他还站在墓碑前,影子在天光中被拉得很长很长。
他没有带花,只有一沓装订好的小册子——那是张继川没写完的论文。张继川曾经说死也要带着自己的论文一起,应泊看着论文封面那一长串的题目,鼻梁忽然一酸。
他终于转身离开。
风还在吹,天色渐暗,应泊背影仍然笔直,却好像被轻轻击碎了一角。
“再见了。”他说。
殉道者的每一封信,如今都像火种,却没有烧向“恶人”,而是点燃了愤怒、歇斯底里、投机者和信徒交织的地狱,尽数烧向那些无力抵抗的更弱者。
哪怕被煽动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也足够搅得这片原本平静的海域不得安宁了。
那天中午,湾河南区爆发了第一场街头冲突。有人在广场举起“人民审判”横幅,大声宣读殉道者的“信条”;有青年自制喇叭,对着交警吼:“体制不是法律!我们要的是公平!”;还有人在网上发起模仿行动,公布所谓“可疑人员名单”,试图用人肉和围堵来制裁他们眼中的罪人。
一小时内,望海市政府被泼上红漆,网络上一段段断章取义的“殉道者语录”以神谕之姿疯传。广场对峙的人群中,有真正的失业者、维权者,也有被煽动的学生,甚至还有彻底陷入角色扮演癫狂的模仿犯。
执勤武警与公安线几度被冲击,有人泼洒汽油,有人举着□□狂喊“把公平还给我”。
局势彻底失控。
应泊坐在办公室里,手机摊在桌上,画面里是现场执法记录仪传回的音画同步资料:烟雾、口号、警棍碰撞盾牌的砰砰声,还有一道沙哑又坚定的声音,从嘈杂中透出来:
“盾阵靠拢,非致命压制,不要误伤群众!所有人听我指令!”
他听得很清楚,是路从辜,被指派上了最前线。
那一刻,应泊的手指动了一下,却没有去拨电话。他知道对方忙,哪怕是说一句“注意安全”,都可能打断对方对局势的把握。他试图劝阻对方,可路从辜只是拍拍他的肩膀,说:
“放心好了,我有分寸。”
他静静地看着那条视频播放完,重播一遍,又一遍。等再抬头时,天已经黑了。办公室的灯没有开,窗帘半掩着,整个屋子灰沉一片。
他靠在椅背上,脖颈僵硬到发酸,闭上眼的片刻,呼吸都不知不觉绷紧了,直到手机震了一下。
他低头,是一封匿名邮件。
邮件没有主题,附件是张图片,正文只有一句话:
“认识他吗?”
图片缓冲的速度很慢。屏幕一格一格加载出来的,是一片血迹斑驳的地面。
破碎的警帽、混乱的人影、地上的指挥耳麦、电棍、电筒滚落四散。一只手臂从画面边缘探入,手腕上缠着熟悉的绷带,血从袖口向外渗出,像被砍断后的断竹竿,半埋在人堆与砖瓦之间。
那一瞬,所有声音似乎都从世界中被抽空。
应泊死死盯着那张照片,整个人像是被冻住了。他没有动,连脸上的肌肉都未曾抽搐一下,眼睛却像是忽然失焦,甚至呼吸都慢了半拍。
照片下方还有第二张,角度拉远,镜头模糊,但分明能看出那是一具被盖上防暴盾的“遗体”轮廓,身形高瘦,脚腕外翻,肩部塌陷。
——是他。
不可能,万一不是他呢?他身手那么好,怎么会……
可张继川被害那天,你也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