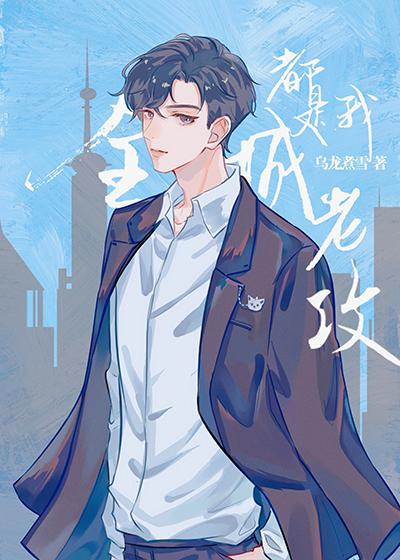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都市科员,我激活了政商决策系统 > 第348章 执尺的人(第1页)
第348章 执尺的人(第1页)
上午九点,省政府新闻发布厅的镁光灯亮得人睁不开眼。
林昭坐在第二排,西装领口微微发紧——这是他第三次穿借来的正装,前两次分别是父亲葬礼和周砚铭落马的通报会。
"全省试点评审机制改革启动。"主管副省长的声音通过话筒扩散,"废除单一进度考核,推行民生健康指数综合评价。"
大屏突然亮起,《云州改革观察》专题片的开场是青阳区新建社区养老食堂的窗口,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正把热乎的红烧肉舀进蓝边碗。
林昭喉结动了动——三个月前这里还是堆着建筑垃圾的荒地,他蹲在工地和老人们聊"要能看见孙子放学"的需求时,周砚铭的秘书正往他茶杯里倒凉白开,说"林科长按流程走,急不得"。
镜头切到陈明远的智慧农场,年轻人举着带屏幕的传感器笑,身后无人机正往田垄播撒有机肥。
林昭想起上周在创业园,陈明远搓着大拇指说"林处,我给系统加了个异常预警,要是有人改数据"话没说完就被自己打断——那时候他盯着对方眼下的青黑,突然明白父亲笔记本里"做事的人眼里有火"是什么意思。
最后画面定在"阳光试点"二维码上,银灰色的方块在大屏上无限放大,像块刻着规则的玉。
台下掌声炸响,林昭却偏过头。
角落有个穿藏青夹克的男人,正用铅笔在皱巴巴的笔记本上速记,笔尖戳得纸页沙沙响——是赵砚清,市试点申报办原科长,三个月前被周砚铭逼得在碎纸机前撕了半宿假数据,现在眼尾的疤还泛着淡红。
发布会结束时,赵砚清的笔记本已经写满三页。
林昭在走廊截住他,对方手里的一次性纸杯还冒着热气:"林处,咖啡。"
"您叫我小林就行。"林昭接过杯子,指腹被烫得缩了缩。
三个月前在纪委谈话室,赵砚清攥着他的袖子哭,说"我也想报真实数据,可周处说不达标就摘我帽子"。
现在男人的指节不再发白,指甲缝里还沾着铅笔灰。
"接下来,想不想回体制?"林昭把咖啡递过去,"不是当棋子,是当规则制定者。"
赵砚清的笔尖在笔记本上顿住,抬头时眼里有光:"能给我支红笔吗?
我想标重点。"
中午十二点,青阳区政府顶楼的小会议室飘着茉莉花茶的香气。
沈清欢推来转椅时,椅腿在地板上刮出轻响——这是她的习惯,怕突然的动静惊到专注看文件的人。
林昭接过她递来的内参,封皮上"改革表演学"五个字被红笔圈着,页脚有省委主要领导的批示:"切中要害,可作试点参考。"
"苏砚舟教授写的。"沈清欢把茶盏往他手边推了推,"她说政策创新易沦为政绩剧场,评审权需独立于执行体系。"
林昭翻到最后一页,自己提出的"熵值模型"被标了荧光黄,旁边批注:"技术制衡范例,可推广。"他手指摩挲着纸页,想起上周在党校讲座,苏教授问"林处长,你相信技术能管住人心吗",他答"至少能让歪心多绕三道弯"。
"她看得准。"林昭合上册子,"可技术再准,也防不住人心歪。"
沈清欢垂眼整理着散在桌上的文件,发梢扫过手背:"但至少,现在有人敢写了,有人敢批了。"窗外的风掀起一页稿纸,正好停在"评者若正,改者有光"八个字上——那是林昭今早抄在笔记本上的,父亲的字迹还带着墨香。
下午三点,林昭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得发烫。
顾轻语的报道《火光里的评分表:一个科员与七座空心试点的战争》刚推送十分钟,阅读量已经破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