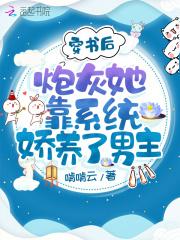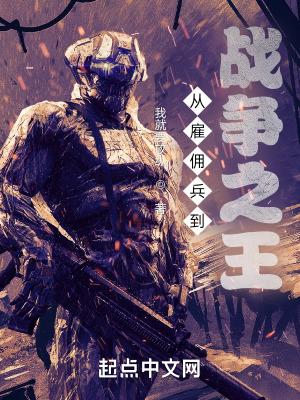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历史许愿墙, 开局拿昏君祭天 > 5055(第15页)
5055(第15页)
但见一片风物寥落,哀草离离,数点萤火照亮了苍茫一片的夜空,远处月色依稀,描摹出一线远山如眉。
天地风景原无异,山还是那时的山,月还是当年的月,只是人事改。
这座汴梁故城,见证了周宋易代,北宋帝业,靖康之耻,海陵建都,贞祐南渡,数次被攻破,又数次从废墟上再度兴起。
最近的一次,它经历了金哀宗时期的战火与瘟疫,随后被蒙古军放弃,夷为平地,早难觅昔时光景。
王清惠抚今追昔,百感交集,落泪在墙壁上题了一首《满江红。太液芙蓉》。
“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客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
这是一个亡国之人,捧心泣血、长歌当哭之作,很快就传遍了江南各地,人人能唱。
汪元量也在墙壁后边,跟着题了一首:
“……人去后,书应绝。肠断处,心难说。更那堪杜宇,满山啼血。事去空流东汴水,愁来不见西湖月。有谁知、海上泣婵娟,菱花缺?”
“愁来不见西湖月。”
这时的他并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一语成谶,这么多人当中,竟真的只有他活到了回归江南,重见那一轮西湖月。
宫人们继续北上,先是到燕京,后来,又去了积满冰雪的苦寒之地,上都哈拉和林。
汪元量一直陪伴在故主身边,一如当年在临安宫中那样。
他本不必如此,因为忽必烈很喜欢他的琴,待如上宾礼。
忽必烈甚至觉得,他是南人中最惊艳的那一个,任命他为使者去主持三山五岳的国祭,并说,“如朕亲临。”
但汪元量拒绝了入仕元朝。
他在燕京,时常去探望狱中的好友文天祥,并为对方抚琴一曲南国乡音,聊表寸心。
他在迁徙北往的路上,始终守住着太后幼主四处流离。
他将很多的行中见闻写成了诗,长吟处,一字一泪,百感成灰。
从兰台锦宴的青灯倦客,到关山万里的浪迹之人,风住尘香花已尽,人间唯剩云边秋。
后人比他为杜甫,将他的诗称为「诗史」,因为每一行文字中都有太多的亡国遗恨。
到后来,十余年过去了,宋这个时代已经成为了历史,一切都已然尘埃落定。
汪元量向忽必烈辞行,一身风霜,负琴回归了江南去。
走前,包括昭仪王清惠在内的十余位故宋宫人为他送行,作十首《望江南》词,让汪元量将这些带回南方的故园去。
她们今生今世注定只能终老于北地,极目所见,唯有积雪满燕山,万里长城横缟带。
那些六街灯火,烟雨阑珊,故园的一切景色,都只能向梦里一见。
梦醒后,依旧隔着永远不可跨越的时间洪流。
忽必烈觉得很可惜,极力挽留,然而,汪元量去意坚决,宁死于南国乡土。
这不是出于对宋廷的忠贞,毕竟他只是个琴师,从未在宋朝正式为官。
但他知道,自己有一件使命,是必须要去完成的……
在浩荡的王朝易代中,没有人会关注到一群北行的宫女在想什么,这些小人物有过怎样的悲哀。
但汪元量记得。
他从燕京南下渡江,跋山涉水,兜兜转转,终于回到了江南。
这一条路,古往今来,很多的亡国之人都走过。
金亡以后,元好问不愿入元为官,独自南下,行经哀宗皇帝的行宫。
见此地早被付之一炬,唯有砖瓦残存,想起当年西山晴雪,与帝王赋新诗的时节,不觉潸然泪下。
“焦土已经三月火,残花犹发万年枝。他年江令独来时。”
江令就是陈朝的尚书令江总。
昔时锦袍玉带,名冠陈宫,亡国后随陈后主北上,年近七十,终被允许归乡,已是两鬓霜雪,重来如隔世。
亡国的悲痛遗恨,从来是一寸山河,一寸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