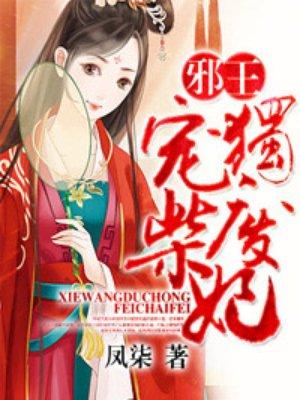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锦衣轶闻录 > 第 49 章(第1页)
第 49 章(第1页)
周啸阑走后,她正往陆心棠所在的乙舍方向走。
“站住。”一声不轻不重的声音在后方响起。赵柔柯闭了闭眼,这声音不看脸也知道是谁。
她内心想着:糟了。这几日一直忙忙碌碌,两位夫子布置的功课,她还一字未动。
她转过身,如愿看到李夫子那张严肃的面孔,旁边是拿着戒尺的王夫子。
王夫子的戒尺在手中轻轻敲打,她感觉每一下都像打在自己身上。
她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鞠了一礼,恭恭敬敬道:“李夫子好,王夫子好。”
李夫子背着手看着她:“既然回了书院,为何不来听学?”
李夫子很少有面部表情,因而再怎么稀松平常的一句话,到了她嘴里就变得严厉无比。
赵柔柯赶紧端正态度,没有丝毫解释,并向两位夫子保证功课会尽数补回,李夫子这才无甚表情地点了点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莫要仗着天赋,怠慢学业。”
赵柔柯俯首点头称是。
李夫子离开后,她抬头便对上了王夫子笑眯眯的一双眼睛:“赵柔柯,你可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啊?”
他这一笑,赵柔柯便知道是要罚抄了。
赵柔柯心理准备做得十分充足,举手作揖,头埋得更低:“学生知错了。”
只听王夫子道:“目无尊卑,戏弄师长。罚抄《礼记学记篇》二十遍,黄昏时提交于我。”
“是……”
眼见王夫子要离开,赵柔柯内心犹豫了一阵,还是叫住了他:“夫子,请等一下。”
王夫子转过身:“何事?”
赵柔柯开了口:“师恩与亲情,他是分得清的。在他心里,是把你当亲人的。”
良久,王夫子知道她说的是谁,没有露出惯常的笑脸:“我知道的。”这么多年来,他都知道的。
“你告诉他,以后隔三差五的,不要大半夜在我房顶上坐着了。他要来,便大大方方来。我年纪大了,经不起他吓。”
他顿了顿,看向她,又继续说:“不过,这也有些日子没有看到他来了。想来是周府比从前热闹许多,这样挺好。”
晌午的太阳被云朵遮住一半,王夫子低矮的背影在地上拉出瘦长的一道影子来。
人只有在自己觉得安全时,才会露出真实的性情来。短短几次,周啸阑只有在王牧之面前,才有一点鲜活气,她能从中窥见曾经那个肆意的少年郎。
江子修失踪返家后,没多久,江子妍曾带着谢礼来过。赵柔柯自知在她弟弟的事情上并未帮上什么忙,婉言谢绝了她的礼。
拐子伏法后,小宝还在原来的地方卖报。有了陆心棠的故事,加上赵柔柯的画,小宝的聪明脑瓜,画本子一路畅销。赵柔柯结了钱,给陆心棠买了一张上好的弓,好让她应对对不久之后的又一次小考。
周啸阑好像比从前更加忙碌,偶尔来书院也不再避着王夫子了,有时带各种各样的零嘴会带两份,王夫子虽嘴上满嘴嫌,可布置下来的功课没有从前那么恐怖。
因而,总会有学子跑来问:“你表兄今日来吗?”赵柔柯这时总是会点头:“来的来的。”
接着便会掏出一叠新出的画本子见缝插针地兜售:“这是新的试阅本。好看再来!同窗有礼,买一赠一。”
陆心棠对她这等财迷做法嗤之以鼻,拿着弓箭整日待在书院练武场,偶尔会问问葛藤伯的近况,周啸阑有探子在梧州,经照看着,目前葛藤伯身体尚安。
日子波澜不惊地过去,转眼便到了秋日,赵柔柯看书看得脑子发昏,想出去走走。明日书院旬休,好些学子回家了,书院很冷清。她一个人走到门口,便看见不远处立了个人。
是江子妍。赵柔柯很久没见到她了。这次的她和以前一点也不一样,身着一身利落男装,捧着一只木箱,也不知道在门口等了多久。身后还跟了一只看上去有些营养不良的骡子。
赵柔柯走上前,闻道:“书院明日旬休,你来找谁?”
![流放后嫁给失忆将军[重生]](/img/15325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