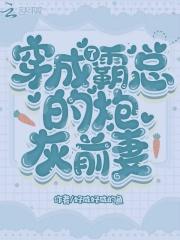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大唐第一女夫子【基建】 > 夜校(第2页)
夜校(第2页)
时下的《九章算经》对于普通人来说也如同天书,主要是《算经》以生活中遇到的数学问题为章节,而并非以数学原理为章节。虽然体现了中国人务实的思想,却也导致了数学研究的停滞。
毕竟农业社会,能用到的数学知识就这么多。而因为问题情境的不同,光算体积的时候边长就有上广、下广、下厚、上袤……等无数个术语。
章文瑛在夜校中教算术时便放弃了以上所有冗杂的术语,而是一律用“长、宽、高、径”来描述。
事实上,成人学算术要比学识字快得多,如今《千字文》教授的进度慢,农妇们的算术却学得飞快。如今早已学会了基础的加减法,背会了九九乘法表,开始丈量自家田亩,根据章文瑛教授的方法来对比田契上的数据是否有误。
农妇们也强烈要求章文瑛先教她们写自己的名字,然后再教《千字文》。然而唐人习惯以家族中排序为名,若是读书人还好说,这群农妇和她们父兄丈夫的名字全是“大郎、二娘……”
这使得章文瑛的教材不知不觉中从《千字文》变成了百家姓,还是她根据扫盲班里姓氏的多少现编的。
每夜上课,农妇们先默写一遍自己的名字,然后从零写到十。接下来齐声背诵《千字文》学到的部分,章文瑛再开始一夜的学习。
这天,班里学习热情最高的张三娘犹犹豫豫地站在了章文瑛面前,扭捏了半响道:“夫人能教我认这份文契上的字吗?”
章文瑛接过文契,一个字一个字地指过去,念给张三娘听。孰料她还没念完,对方便已经潸然泪下。
最后张三娘哽咽着说:“夫人真是活菩萨,没有夫人,否则妾身不知道要被这份文契骗到什么时候。”
正在地上拿着炭笔练习着今日所学《千字文》的字的妇人们都停下来,支着耳朵听张三娘哭诉。
原来张三娘家里是个商户,丈夫早早地去世,自己也无儿女,一个人守着丈夫留下来的逆旅过活。
张三娘手脚勤快,馆舍打扫得干净,做饭也好吃,价格也公道,很多从西面前往杭州做生意的商人都常住她家,日子就这么太平地过了下去。孰料前几年蔡县令来此,家里人看中了她这间铺子,想要出高价买下。
虽然蔡明府给的钱财足够她衣食无忧,然而那间逆旅毕竟是张三娘亡夫给她留下的唯一念想,她不大想变卖,也不敢得罪县令,便坐在柜台前垂泪。
一个从闽南前往长安赶考的士人听到了她的苦恼,笑道:“这有何难!你跟我签了这份文契,我保证县令再也不来买你的逆旅!”张三娘病急乱投医,便跟他在文契上画了押。好在她留了个心眼,士人想要把文契带走,张三娘死活不同意,说带走了岂不是白签了文契,便把一式三份的文契全留下来了,跟士人约好待他赶考回来后再把其中一份文契给他。
后来县令家人果真再来催促张三娘,张三娘给他看了这份文契,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张三娘本以为事情就此终结,孰料前几日正好遇见当年给蔡明府做活的一个下人,两人便聊了几句,对方听说她依旧守寡时表现得极为诧异,道:“可是你给我们看的那份文契上……”
那人自知失言,即便张三娘再三询问也不肯回答,匆匆走了。张三娘实在奇怪不已,便带着其中一份文契来找章文瑛。
“文契全在你这里吗?”章文瑛询问道。
“本来全在的,有一份被蔡明府家人拿走放官府了。妾身当时也没多想,觉得他们可能是做个留存,若妾身把铺子转卖给他人可以借此起诉或要挟。没想到是妾身错怪明府了。”
章文瑛拍案而起:“我们明日就去县衙,找县丞把那份文契拿回来全撕了!”
原因无他,那份文契居然是一份自愿为奴的契书!上面写了张三娘子携带自己的旅店成为士人胡成启的妾室,此间逆旅为胡成启所有。
既然逆旅不再由张三娘子说了算,蔡县令家人自然不会再来找她。可怜张三娘,差一点就既没了丈夫的旅店,又从良籍变为贱籍了。
章文瑛也没了心情,当夜早早地下了学,第二天难得地起了个大早,跟着张三娘到了县衙。没想到居然遇见了一个熟面孔。
新登县丞,赫然便是新婚之日帮着杜稜作诗的那个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