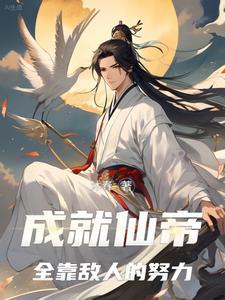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全京城热搜被我承包 > 黑红营销(第2页)
黑红营销(第2页)
“要的就是黑。”昭虞眼尾上挑,带着点狡黠,“黑透了,才能红。”
不出一日,京城就被这童谣淹了。
清晨的早市上,挑着担子的货郎刚吆喝两声,就被一群小孩围着唱,茶寮里的说书先生刚敲醒木,底下就有孩童接腔,连国子监的门口,都有穿长衫的学子摇头晃脑地哼。
调子简单,词儿直白,想忘都忘不掉。
桑枝从外面采买回来,手里还捏着个被小孩塞的泥人,捏的竟是个鬼鬼祟祟揣着字纸的小人:“小姐,您看这。。。连泥人都开始糟践陈公子了。”
昭虞却拿起泥人端详:“捏得还挺像,我们去看看,公告栏上有没有新动静。”
果然,南大街的公告栏前已经围满了人。有人贴了张匿名的揭发信,说亲眼看见陈临赋深夜溜进书铺,还有人画了幅画,把他画成个贼眉鼠眼的小老头,怀里揣着卷比他人还高的字稿。
“这不是胡编乱造吗?”有个书生愤愤不平,“陈兄虽出身寒微,却断不至于。。。”
话没说完就被人打断:“你认识他?怕不是一伙的吧?”
“就是,不然怎么没人替他说话?”
议论声嗡嗡作响,像一群被捅了的马蜂窝。阿野雇的那几个“同乡”混在人群里,见缝插针地叹气:“唉,他小时候就偷过先生的讲义,那时我们都劝他,谁知。。。”
这话一出,更没人替陈临赋辩解了。
昭虞站在对面的绸缎庄门口,看着公告栏前越聚越多的人,对桑枝道:“去告诉阿野,让他的人收着点,别太刻意。”
“小姐,真的没事吗?”桑枝看着那些不堪入目的画,“再这么传下去,陈公子就算洗清了冤屈,也抬不起头了。”
“抬不起头?”昭虞指着人群里一个摇头晃脑唱童谣的小孩,“你看那孩子,他知道陈临赋是谁吗?他就是觉得调子好听。等咱们想让他抬头时,这些人照样会夸他。”
京城里的流言,正闹得沸反盈天。
过了几人,阿武照常来汇报每日的情况,临走时又道:“对了,小姐这两日讨论的人好像少了些,大家听腻了似的。”
“正常。”昭虞早有预料,“再劲爆的戏文,听多了也会烦,让阿野来见我。”
阿野赶来时,还带着股酒气,想来是刚从茶寮打探消息回来。“姑娘,您找我?”他挠挠头,“是不是还得再加点料?我让那几个同乡再编点新故事?”
“不用。”昭虞摇头,“再编就假了。我问你,前阵子让你贴的那些诗集,怎么样了?”
阿野愣了愣,这才想起前几日昭虞让人抄了些陈临赋写的诗,贴在公告栏和书铺门口。
“嗨,别提了。”他面露难色,“除了那些学堂的先生和老秀才,没人看。有回我看见个挑夫,对着那诗瞅了半天,说这字歪歪扭扭的,还不如他儿子写的尿床字好看。”
昭虞却笑了:“挑夫不看没关系,你说的那些学堂先生,看得仔细吗?”
“仔细!”阿野点头,“有个白胡子老头,还带着纸笔抄呢,边抄边叹气,说简直才华横溢。”
“那就够了。”昭虞道,“你再让人抄些不一样的,别光抄诗,把他写的策论也抄几份,照样贴在公告栏和书铺门口。不用刻意让人看,就那么贴着,有人看最好,没人看也无妨。”
阿野一脸不解:“姑娘,这能有用吗?上面连署名也没有,那些酸秀才看了,顶多叹口气,又不能帮着说好话。”
“谁说要他们说好话了?我要的是,让他们知道—这个‘窃书贼’,字里是有东西的,只是现在风言风语太多,大家都没法以正常的眼光去看待。”
阿野虽不懂,还是乖乖领命去了。桑枝看着他的背影,忍不住问:“小姐,这到底是图什么呀?又让人家骂,又让人家看诗,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不矛盾。”昭虞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个“红”字,又在旁边画了个黑圈,“黑是让所有人都看见他,红是让该看见的人看见他的好。那些骂他的人,记的是‘陈临赋’这三个字;那些看诗的人,记的是这三个字背后的东西。等这两样凑齐了。。。”
她没说下去,只是笔尖在“红”字上轻轻一点,像是落下一个印记。
接下来的几日,京城里的流言果然渐渐淡了。
童谣还在唱,却没那么响亮了,《偷书记》的戏票也开始打折,看客稀稀拉拉的。只有公告栏前,偶尔有几个老秀才驻足,对着新贴的策论点头赞赏。
一切都按正常的流程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