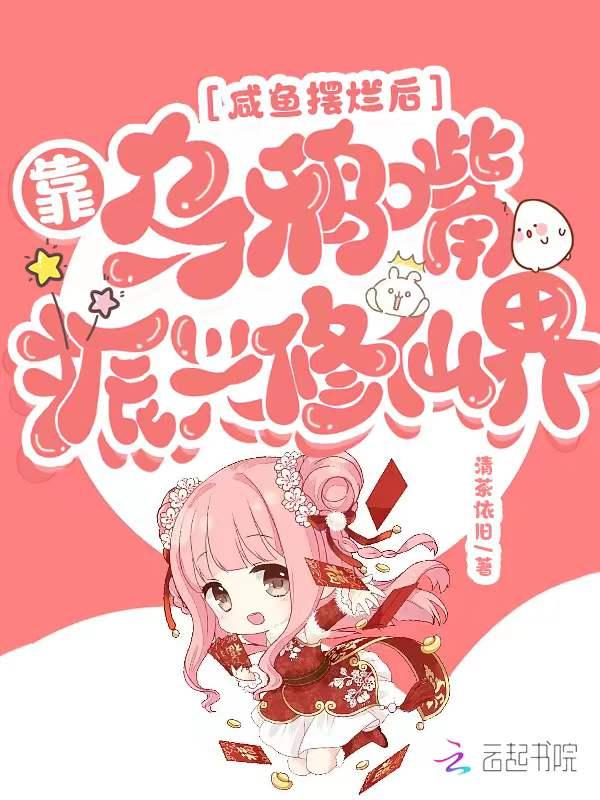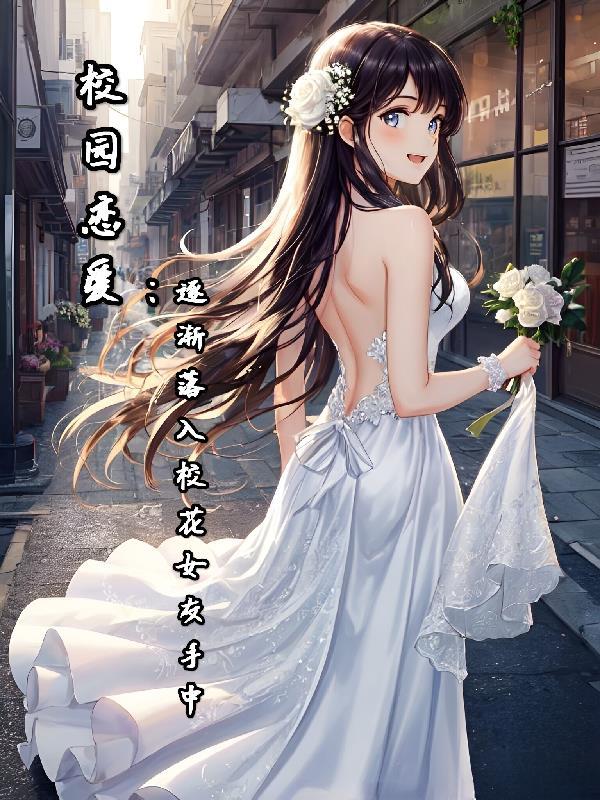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从罪臣之女到一代大儒 > 八卦(第1页)
八卦(第1页)
袁微识一脸钦佩:“老丈真是见多识广,运气也好!能在那种地方全身而退,还把这皮子生意做得这般稳当,真真是大本事!”
这马屁显然拍得老汉十分舒坦,他哈哈一笑,脸上的褶子都舒展开不少:“混口饭吃,混口饭吃罢了!小娘子你识货,人也爽利!这样,看在你我有缘的份上,这块皮子,半吊钱!不能再多了!这年头,能平安把货弄出去才是真本事,价钱嘛,都是虚的!”
袁微识心知这已是老汉愿意出的最高价了。
她不再犹豫,爽快地将皮子推过去:“好,就依老丈的。多谢您照拂了。”
交易完成,气氛似乎更融洽了些。
袁微识将铜钱小心系到袖子里,随意地闲聊道:“说起来,我们初来乍到,听说这嘉峪关的守备徐大人,是个厉害人物?有他在,想必那些游兵也不敢太放肆吧?”
“徐乱?”老汉脸上的笑容淡了些,叼着烟锅,眼神变得有些复杂。
“那是个活阎王!杀起人来眼都不眨!手底下的兵,比草原上的狼还狠!有他在,嘉峪关这一线,确实安稳不少,那些零散的鞑子轻易不敢过来。”
他顿了顿,左右瞟了一眼,声音压得更低:“不过嘛,小娘子,这话老汉也就跟你说说。这位徐阎王,本事是大,那上头,可未必待见他啊!”他伸出枯瘦的手指,隐晦地向上指了指。
袁微识心里咯噔一声。
“这是怎么说?老丈是说燕王殿下吗?”
老汉没直接回答,只是吧嗒了一会烟嘴,才又重新开口。
“燕王殿下纵横北疆,见过多少世面?那是跟着先帝打天下的人物!徐守备这种性子,锋芒太露,不懂收敛。他杀鞑子狠,对自己人,对那些不听话的豪强、不按规矩来的商队,下手也从不留情!挡了多少人的财路?又碍了多少人的眼?燕王殿下身边,可不止他一个带兵的将军!”
“听说,只是听说啊,”他把手搭在嘴上,压低声音:“他在北京城那边,根基浅得很,没什么得力的靠山。全靠一身不要命的狠劲撑着。可这年头,天下承平,除了北边这些小喽啰,还有哪能打仗?光会砍人,路能走多远?”
袁微识皱起眉头。
这可和她听说的不一样。
若是徐乱真的只是个莽夫,那进黑山峪的烟雾弹是谁放的?或许是他身边的幕僚?
那这个幕僚也是她必须要重点关注的。
袁微识忽然想起那一天徐乱马后的青衣文人。
那天她太慌乱,略过了很多信息。现在想想,徐乱和燕王的关系,比她想象的更复杂。
“姐姐?”
文柏见她久久不语,轻轻扯了扯她的袖子。
袁微识回神,看到文柏苍白的小脸,连忙对那老汉笑了笑:“多谢老丈指点。这世道艰难,我们小门小户,只求安稳度日罢了。”
她拉了文柏,“天色不早,我们还得去买些东西,老丈就此别过。”
老汉也拱拱手,坐了回去,又叼起烟锅,眯着眼,恢复了混日子的模样,仿佛刚才的谈话从未发生过。
袁微识拉着文柏继续向前走,文柏沉默一会,终于忍不住小声问:“长姐,那个老丈说的,徐乱他会不会很危险?那,那你——”
小小的少年心思写在脸上,徐乱是姐夫这件事已成事实,他开始为他担心,又有些得意,仿佛徐乱马上就要被贬斥。他活该!
但是那样长姐也会跟着吃挂落!
他皱着脸,不知道是该为这件没影儿的事高兴,还是担忧。
袁微识猜到了文柏的心思,忍不住笑弯了眼。
“文柏,不要做无谓的担忧。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我们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手里能抓住的东西。”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冻得通红的手。
这双手,能提笔写锦绣文章打遍金陵无敌手,能捏着银簪刺向恶徒,也一定能长成一柄利剑,斩杀恶人,为袁家平反。
继续往前,逐渐靠近镇子的中央。
道路似乎平整了些,虽然依旧是黄土路,但两边用碎石头垫了垫,污水也少了些。
道路两旁的铺子也逐渐干净起来,各种吃食摊子琳琅满目,愈发精致。
巨大的烟火味让心情不佳的袁微识面色和缓,更不用说小少年文柏,他目光雀跃,这么多天,第一次活泛起来。
往前走,一个避风的角落里,支起一顶毡布棚子,棚子下面,一口大锅架在炉子上,锅盖掀开一角,白色蒸汽滚滚喷出,浓郁的鸡汤味随着一缕缕白烟,飘到文柏鼻子里。
棚子前面立着一块粗糙的木牌,黑炭歪歪扭扭写着“馄饨”二字。
一个妇人拿漏勺伸进去,捞出十来枚各个饱满大肚的馄饨,用锅盖接着放到粗瓷大碗里,又转身在另一口小火慢炖的大罐子里舀出一碗热腾腾的白汤,利落地倒在大碗里,随即用铁叉子抄起碗底,快走两步放到旁边的小木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