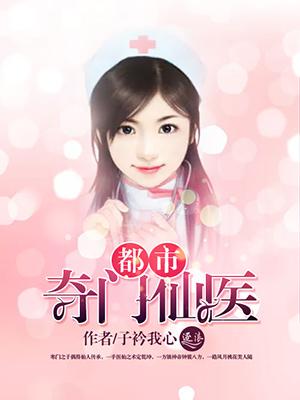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王爷他总想蹭我功德 > 侍女(第2页)
侍女(第2页)
这里是王府中收发文书的签押房,后院中的亲眷,若是有家书,亦可送到此处,会有管事的负责收发。
绕过前厅,青瑗来到背后的鸽房,这是王府奴仆书信往来之地。
她抬起腿,正欲迈进门槛,忽然听见内里传来人声。
“周管事,您行行好,帮老婆子念下闺女写的信吧!”一个沙哑迟缓的老妇声音带着恳求。
“去去去!没看我正忙着?别在这儿添乱!”
青瑗跨过门槛,只见一个身穿褐色绫衣、身宽体壮的中年男子不耐烦地粗声驱赶他身前的仆妇。
那个站在鸽子笼旁的男子,他就是周管事?
而他身旁,那仆妇求他不得,低声啜泣起来。
周管事依然不搭理,青瑗见此觉得不忍心,于是几步走向前去,见那仆妇穿着短衣窄袖,正佝偻着背抹泪。
待走得近了,青瑗才闻到仆妇身上的气味不太好闻,像是牲畜粪便的味道。
她应是王府里的某个粗使的仆妇。
“老人家,您怎么了?”青瑗温声询问。
仆妇见有人问询,慌忙用袖子揩脸,转过头来。青瑗心头微惊——只见她半边脸上覆着大片红褐色胎记,衬得那张饱经风的脸庞更显骇人。
“姑娘,您……您识字吗?”仆妇眼中泪光闪烁,满怀希冀。
青瑗抑下心中惊骇,点了点头:“识得。”
仆妇听到肯定的回答,眼中亮起微光,颤抖着手从怀里掏出一封书信来。尽管她的衣服皱巴巴的,但这封信却很平整,显然被悉心保存着,“老婆子不识字……这是俺闺女嫁去黄山县后,头一回给俺写的信,您可以帮俺念念么?”
青瑗了然。方才定是那位周管事嫌她,不愿念信,而她一时又找不到第二个识字之人,才着急上火。
那书信在怀中揣了一阵,也沾染了些浊臭之气。青瑗喜洁,但见她殷切目光,仍接过书信,轻声诵读。
信中,仆妇女儿诉说着嫁人后的苦楚:丈夫酗酒,醉酒之后拳脚相加……
仆妇越听越急,双拳攥紧,浑浊的泪水汹涌而下,嘴里不住念叨:“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
青瑗亦感无措,捏紧了手中包袱。里面还装着几张化厄符,可在这挣扎于尘世泥泞中的人面前,祖师的保佑,看起来不过是苍白的慰藉。
“老人家,要报官么?”
青瑗既没有说“可要算上一卦?”,也没有说“此乃三清化厄符,可驱邪除厄”。她说了身为一名合格的道姑不该说的。
若是师父在此,又要骂她多嘴了。
这世间女子,出嫁从夫,从此半生的幸福,都寄托在所嫁之人。
她曾在青云观时,听过许多女香客的祷告。她们所托非人,无不是求丈夫浪子回头,幡然悔悟,或是再求得一子,望以此换来夫妻和睦。
但没有一人,是去求和离的。她们大抵是觉得,只要还没有到典妻卖女的地步,这男子还并非无可救药。
她已经做好了被仆妇反过来埋怨的准备。
那仆妇听完,也不答,只一味默默垂泪。青瑗就这么安静地陪着。
她也曾听说过,富贵人家的女儿,若是受了气,会有娘家支持和离。可普通人家,没有厚实的家底,世人会劝“忍”字当头,想开些罢。
世人眼中,似仆妇女儿这般,若是有娘家兄弟出头,那已是万幸。若是没有,那大抵只能怪她命不好。
仆妇哭干了眼泪,像下定了某种决心似的,哀戚道:“姑娘,您能帮我写一封回信吗?”
青瑗点点头,去找周管事借来笔墨。
周管事将笔墨递给她,摇摇头,有几分嫌弃道:“小姑娘,你管那老婆子做什么?”
青瑗向他谢过了纸笔,也不作解释,走到桌子前,铺纸提笔,“老人家,您说,我写。”
仆妇深吸一口气,哑声道:“好!”她抬起灰扑扑的袖子擦干了眼泪,“您就写——别管那个挨千刀的短命鬼,你快回来,娘带你去报官,和离!”
青瑗执笔的手一顿,愕然抬首。
“就是跟娘回来挑马粪,也好过留在那被人活活打死!你要是不愿和离,不报官也行,他若要是再敢动你一根指头,就给娘写信,娘提着马刀来剁了他!”
仆妇口齿不清,青瑗凝了神才听真切。她埋下头,奋笔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