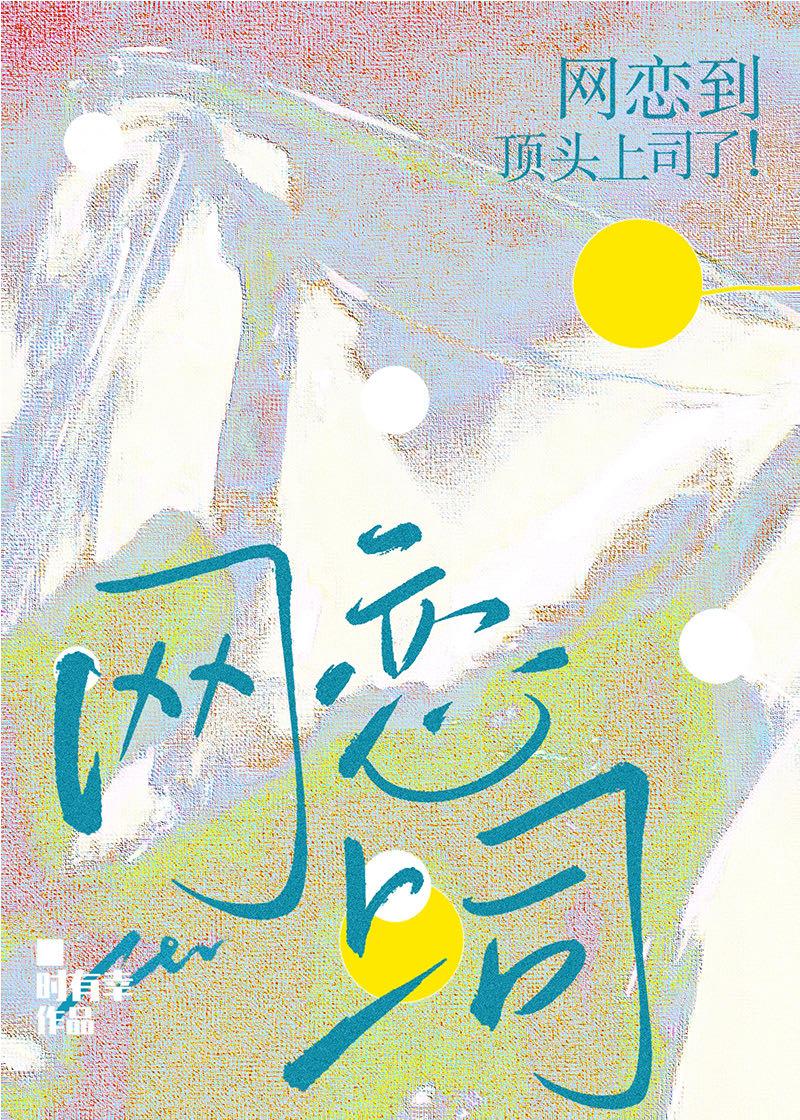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琼珠碎又圆 > 恒卦(第2页)
恒卦(第2页)
裴敬宏的声音有点变调:“大哥就是在这间屋子去的,难到是大哥显灵?!”此言一出,恐惧亦如黑暗一般,在众人心里蔓延。
裴敬宽高声道:“快叫人进来,把灯点上!”
裴烈离门最近,他打开门,欲唤下人来点灯,却猛地僵在原地,一脸惊骇地指着院角月门方向,“快看那里!”
众人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只见惨白的轻烟缭绕,一个身影脚不沾地地飘进院中,立定在繁茂的桂花树旁。那身形样貌,赫然就是裴敬宣!只是面白如纸,声音冰冷透骨又带着炽烈的激愤:“熙儿,我待你不薄,你为何害我!”
“爹!”裴照低唤一声。
“伯父?!”
“大哥?!”
众人纷纷出声,满眼难以置信,屏息凝视,不敢动弹。
裴夫人哽咽道:“老爷,你有什么事不能瞑目吗?”
裴敬宣面无表情地抬手一指,“是裴煕谋害了我!”
众人的目光瞬间又凝聚在裴煕身上。不同于方才的狂喜,裴煕感觉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他惊恐跪地,语无伦次,“不,不……我没有……”
“孽障,你还要抵赖,看看这是什么!”裴敬宣宽大的衣袖一扬,飞起一块白布,如同招魂的幡一样,悠悠荡荡,飘落在裴煕面前。裴煕一见那块染了青汁的苎麻白布,瞳孔骤然收缩,面如死灰,身体也如筛糠般剧烈颤动。
裴敬宣的声音如九幽寒风:“你是在此处说,还是随我去阎罗殿说!”
巨大的恐惧狠狠攫住了裴煕的心智,他声嘶力竭叫道:“父亲饶命!父亲饶命!我、我想借接待使团的机会步入仕途,父亲不允,还说送走使团就、就开宗祠,断绝父子关系,我没法子才……”
裴烈难以置信地瞪着他,“你竟真的弑亲杀父!”
裴煕蓦地抬头,眼中闪烁着扭曲、近乎癫狂的“理直气壮”,“我行事前占过卦了,是恒卦!‘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是上天同意我这么做的!”
裴照的声音冷利如冰锋:“第几爻?”
“九、九三爻……”
裴照一字一句,清晰念出爻辞,宛如审判:“‘恒卦九三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九三以阳居阳,其位虽正,因其执心不定,德性无恒,终招致灾祸。”
裴氏一族世代浸淫《易经》,无需解释,都解其意,纷纷默然摇头。
裴照道:“你是如何下手的?”
裴煕乞求地看着众人,在一片或鄙夷或憎恶的目光中,神志接近崩溃,机械般哆嗦着回答:“我偷偷、摘了乌头叶,趁夜深人静,只有父亲、一人在书房,我、我装作悔改请罪,给他敬茶,在茶中放了乌头。”
裴照看他恍惚的神情,恨意喷薄,指尖深深嵌进掌心,厉声质问道:“你当时没发现,爹在书案上留下的‘革’字吗?他彼时已改变了心意,要革旧鼎新。你白白害死了他!”
裴煕如遭雷击,双手抱头,发出野兽般的嘶吼。
裴敬宣转身,飘然而去。
待烟雾消散,众人方如从噩梦中惊醒,只是在地上翻滚、陷入癫狂的裴煕证明,这不是梦。
裴敬宏惶急道:“这……这要是传出去,裴氏的百年清誉可全毁了!”
裴照看着裴敬宽,目光灼灼,不容回避:“二叔,以为如何?”
裴敬宽心虚,捶胸顿足道:“没想到这孽畜狼心狗肺,竟行此悖德悖伦之事!我有愧于大哥啊!”
裴照环顾众人,众人在她有分量的注视下静默下来,她方缓缓开口:“父亲亡魂自幽冥归来,亲手揭开了真相,如今魂灵离去,当是了无挂碍了。裴煕自作孽,已遭天谴。若是诸位没有异议,我明日便禀告公主,父亲风疾突发,不幸病故。后事也可操办起来,让父亲入土为安。”
她将“风疾突发,不幸病故”咬得特别清晰,周身气场沉稳果决,叫人心头一凛,自是无人有异议。

![我貌美娇弱但碾压副本很合理吧[无限流]](/img/806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