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小说网>开国女帝夺权记 现实向 > 不满(第1页)
不满(第1页)
可是犹豫了半天,他还是来到了观南的营帐,见到了头风发作的观南。
观南感到自己脑中的一切几乎被尽数搅碎。在反反复复的病痛与劳碌的摧折下,她的意志濒临崩溃,已经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有泪水静默流下。陈太医非常熟练地隔衣针刺隔腧穴,用香艾膏涂抹她的太阳穴。
恍惚中,她觉得上百把兵器指向她的身体。但随后,一个温暖的怀抱以及那宁心静气的鸡舌香气将她包裹,她的神智慢慢回笼。但转瞬间,她就被献祭给了敌国,当众行凌迟之刑。高台之上,她又见到那个从容的身影。
哪怕灭唐在即,观南心底的恐惧都从未彻底消逝。
她抱起了双膝,泪水慢慢止住了,但是眼眸中没有一丝神采。仿佛眼眶中嵌入的是两个珠子,不声不响,整个人凝固成一座石像。
李洵明白这种神态的含义,那是一种心死的默哀,是对现实的彻底失望。原来掌无上权柄的陛下也会感受到这份悲哀吗?他突然对陛下生出了些好奇与心疼。
"臣晏江请陛下次对。"
观南尚存稚气的面庞上再度出现浓重的悲哀,沉默了好一会,她开口:"皇后出去吧。"
李洵张了张嘴,却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出口。他默默退了出去,但看向观南的眼神已经不只是最初的恭敬,而是多了一分自己的情愫。
一位内臣进来问话,"陛下还……"
"宣。"
深夜里,晏江的面色已有些疲惫。他与李洵擦肩而过,李洵低着头,目不斜视走出观南的营帐。而晏江探寻的目光落在他的脸上,他瞬间感到脸上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痛感。晏江垂目,似乎是对他的反应有些不屑,转头看向观南。
观南苍白的面孔上疲态尽显。
"这么晚了,什么事?"
"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陛下先听哪一个?"
"那就先说好消息吧。"
"好消息是,唐君已死。"
"怎么死的?谁杀的?"
"李翰海。他并不像唐元捷说的那么一无是处,虽然没有彻底击溃唐军,但已经打穿了荀忠的防线。后来,他又在撤退途中,一箭射杀了唐君。如今,那荀忠,不过是困兽犹斗罢了。"
观南被吓清醒了,震惊地看着晏江,脑海中浮现起唐元捷的话语。难道,他劫走了军报?
"另外,臣要检举枢密使唐元捷干扰皇城司的工作。"
"你是说,荀忠那里的情报被唐元捷扣下来了?"
"是。"
"可是朕早晚都要知晓此事,他为何要做出这样的事情。"
"陛下是被李氏逼着交出那三个至尊之位的,未必对李氏没有怨怼。他兴许是想就此刺激陛下杀了李翰海,这样,他既可摘下胜利的果实,又能除掉这个可能夺他兵权的政敌。"犹豫了一阵,他又说:"臣知晓良将难得,可陛下任由唐氏父子独揽军权,恐怕也会生出祸患。"
"可他们毕竟于国难之时,仍旧忠于大吴。"
"陛下,那唐元捷,可未必忠于陛下。"
"他不是也没有叛变吗?"
"他是个聪明人,当时他既没有兵符在手,也没有情报在身。而他的儿子还在外面谋划着颠覆荀忠,他投敌拿不到太好的价格,而不投敌也不至于丧命。反倒是静候事态发展才是最好的选择,如何算得上忠臣。"
观南茫然地盯着一片虚空,"若是如此,朕还有何人可信?"
"这世上本就没有绝对的忠臣,也没有绝对的能臣,更没有绝对的廉臣。这其中的权衡取舍之道,本就是陛下需要谨慎考虑的。还望陛下莫要再轻信于人了。"
"那你以为那唐既白,可是能接替其父之人?"
"若论才华,唐既白整体上用兵谨慎,却从不放过战机,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帅才。但是,他却也是个彻底的孝子,若是让他接替其父之职,怕也只是换得了阵前之人,换不了幕后之主。更何况,这古往今来,又多少人是只可同甘,不能共苦的。这今后的事,谁又说得清呢?"
"那晏卿你呢?朕又是否能相信你?"
观南审视着面前的臣子,但那名臣子没有显露出半分怯色,"陛下已经有答案了,不是吗?"
"如果朕非要你给出一个答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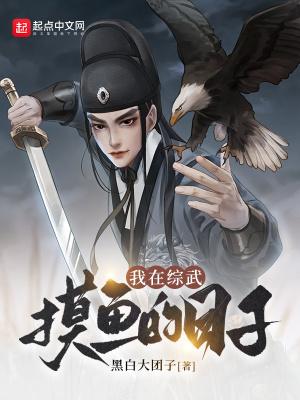
![拯救被pua的主角受[快穿]](/img/1455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