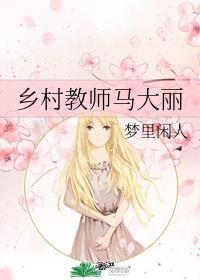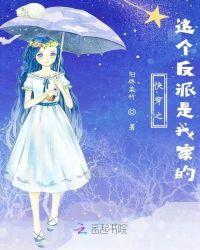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夏夜、晚风和我们 > 第一章(第1页)
第一章(第1页)
《夏夜、晚风和我们》
第一章
春分都过了半月,雨丝还跟扯不断的线似的,斜斜地织在黛青色的山峦间。
东岚村隶属屿城,近年来屿城发展飞速,底下乡镇也纷纷探索出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唯有茶乡东岚村,因为隐匿于重峦叠嶂的山间,不好发展现代化经济,从山里走出去的青年人才没几个愿意回来的,久而久之,东岚村就变成了老人小孩居多的留守村。
夏绵蹲在姥姥家的堂屋门槛上,盯着手机屏幕上跳动的后台数据,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膝盖,牛仔裤上沾着的泥点子簌簌往下掉。
“小绵,真要这么弄?”夏绵的姥姥邱云裹着厚棉袄坐在竹椅上,手里摩挲着半干的茶青,斟酌道:“咱东岚茶讲究的是“一沸鱼目,二沸珠泉”,哪能像街头卖唱似的对着镜头吆喝?”
夏绵抬头,露出一截白皙的脖颈,虽然她眉眼间那股子都市白领的精致还没褪干净,可开口却是实打实的接地气:“姥姥,现在卖茶不吆喝不行啊,再守着“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个旧理,咱们下半年的药钱就得喝西北风。”
她晃了晃手机,屏幕上是她熬夜做的PPT截图:“您看啊,“共享茶园”,六百九十九块认养一棵茶树,全年四拨新茶包邮,每月直播采茶炒茶,跟我当年教您玩的企鹅农场一个道理,简单来说就是把虚拟的变成真的。”
夏绵说得自信满满,可邱云却是叹了口气,指着墙角那堆蒙尘的炒茶锅:“你呀,在城里当那什么化妆公司的总监当惯了,说话办事跟打机关枪似的。咱种茶的,讲究个“文火慢炒”,急不得。”
夏绵笑而不语,蹲下来帮姥姥理了理衣襟,不小心碰到老人手腕上凸起的青筋,心里顿时软了软。
三个月前她接到邻居电话,说姥姥采茶时突然晕倒昏迷不醒,她连夜从屿城飞回来,看着ICU里插满管子的老人,当场就拍板辞了职。
年薪近百万位数的工作说丢就丢,前老板在电话里骂她疯了,可夏绵知道,没什么比姥姥更重要。她打小没爹妈,是姥姥背着她在茶山上爬了十几年,用采茶换来的钱,供她从东岚村读到了大城市。
“不急不行啊。”她拿起桌上的药盒,指着上面的标价,“这进口药一盒顶您炒十斤明前茶,咱不单靠卖茶,得搞点新花样。”
姥姥家的茶铺开在山脚下,光绪年间的老招牌被雨水洗得发黑,“东岚春”三个字还透着苍劲。
只是这几年年轻人都往外跑,镇上的新茶商又总压价,去年冬天连炒茶师傅都被邻县的茶厂挖走了。邱云住院那阵,几亩老茶园差点就被村里的二赖子用低价盘了去。
但现在,夏绵早就盘算好了。
东岚山的茶叶好,可惜藏在深闺人未识。城里年轻人现在就吃“原生态”和“参与感”这套,把茶园搬到线上,让他们看着茶树从冒芽到成茶,既能卖情怀又能卖高价,简直是完美的商业模式。
夏绵说干就干。
她的“共享茶园”方案通过村书记那关后,就联合加入她方案的茶农一起把村子里的茶园翻了一遍,她还买了监控设备和直播支架,连账号名都想好了,叫“茶门信徒”。
昨天调试设备时,村里的半大孩子围着她的手机叽叽喳喳,吓得她姥姥的那只老黄狗对着镜头狂叫,还差点把支架撞翻。
“时辰到了。”
邱云突然坐直身子,指着墙上的挂钟:“你姥爷当年说,卯时开采,茶气最足。”
夏绵一看时间,六点整。
她麻利地穿上雨衣,把手机架在茶园边的老松树下,镜头正好对着那片刚冒新芽的茶树,凉凉的雨丝落在镜头上,晕开一片朦胧的绿意。
“家人们早上好,这里是东岚山共享茶园的首播现场。”
她对着镜头挥挥手,脸上是职业性的微笑,眼神却不自觉地瞟向旁边围观的几个老人,“看到我身后这些茶树没?今天开始,它们可以认养啦!”
话没说完,人群里爆发出一阵笑,王阿公拄着拐杖敲了敲泥地:“小绵,你这是要给茶树找干爹干妈?”
夏绵眼睛一亮,顺势接话:“差不多!认养了就是茶树的荣誉主人,我每天直播给您看它长多高,发了多少芽,采下来的茶叶第一时间给您寄过去,绝对比您对象还贴心。”
这话说得直白又俏皮,连抱着看热闹心态来的路人都掏出手机开始拍,夏绵眼疾手快,立马把镜头对准王阿公:“阿公您看,这棵是百年老茶树,当年还是您跟我姥爷一起栽的,认养价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元,送全年茶席体验,您要不要给它当荣誉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