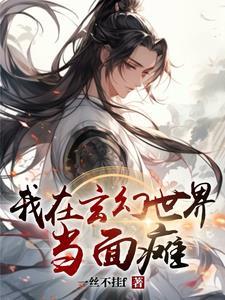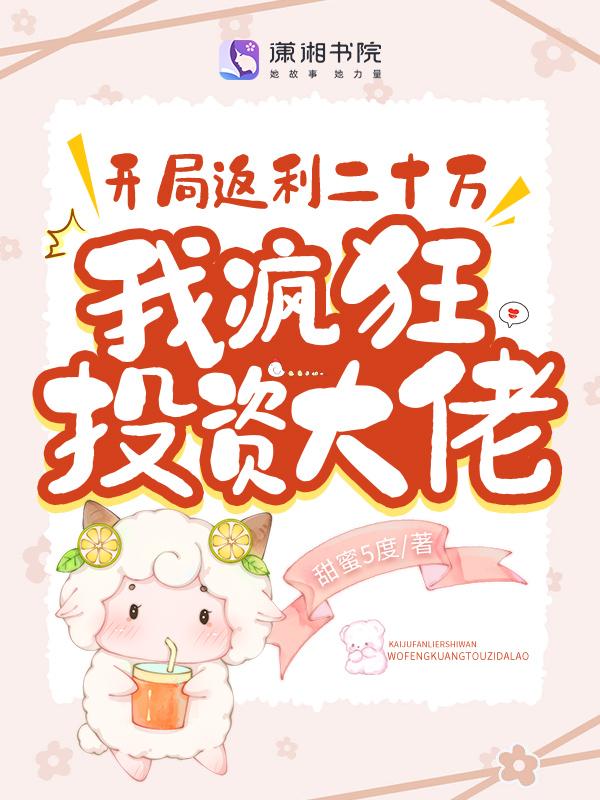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带客栈系统穿武侠 > 第二十四章(第2页)
第二十四章(第2页)
“骸骨分属于十六名幼童,年纪应在三岁到十二岁不等。”
严县尉闻言,眼中最后一丝希冀也随之湮灭。正欲开口,却听杜仵作继续道。
“唯丁复所持之串,应是人骨中掺入了兽骨。”
“此话怎讲?”严县尉遽然离座。
“大人明鉴。”
“人骨骨质较薄,色呈牙白。兽骨则质地粗厚,色偏灰白。”杜仵作擎灯近照,将两盘骨珠映得通明。
“大人若存疑,不妨将两者投入火盆之中。若是人骨,燃之有焦羽之臭。若是兽骨,焚之则似石灰气味。”
严县尉依言,正要吩咐左右去取火盆,却听杜仵作又道,“大人取了火盆,不妨再取些麻油来。”
《洗冤录》曾载,取骨置热油中,新者油浸入,久者不入。
未时正刻,趁着天色尚明,众人移步庭外。
林巡检捧着那两匣丁复的骨珠,因尚有幼童下落不明,案情急迫,为了节省时间,众人将庭院一份为二。
许大夫据东隅,辨兽骨人骨之别。
杜仵作居西侧,验骨殖新旧之分。
“方才检验,这串骨珠之中,兽骨部分大小统一,人骨部分则不然。”
林巡检切齿道,“适才丁复那厮已然招认,是他指示那妖道,将孙小公子的头骨、指骨处尽数制成念珠。。。。。。”
“这便是疑点一。”杜仵作打断道。
“幼童颅骨薄脆,且形状曲面不规则,若强行打磨,极易碎裂。若要切割,唯有顶骨平坦处或可勘用,但也仅能制成铜钱般大小。”
“再者。”杜仵作取出几枚骨珠示以众人,“这些骨珠色泽不一,或呈垩白,或呈牙黄,显非同源。”
说话间,一旁三个铜盆中以文火煨热的麻油已沸如蟹目。杜仵作与另两名医者各取三枚色差明显的骨珠,投入热油之中。
“大人,若为新骨,吸油当如牛饮,若为陈骨,则油星不入。”
一炷香后,三人将骨珠捞出,置于白绢之上,细辨其孔窍油迹,分别呈验于严县尉。
杜仵作捧上手中白绢,“此三枚骨珠,孔内油渍浸润,当是近年新骨。彼六枚通体澄澈,应是年逾三载的陈骨。”
严县尉俯身细观,果见杜仵作那份,白绢之上,油痕清晰,如血络蔓延。
彼时,许大夫亦已验明,丁复那串念珠,确是在人骨中混入兽骨所制。
严县尉喃喃道,“如此说来,慧剑尚存一线生机?”
或许是青阳取血后,出了什么变故,致其未能取骨,只得鱼目混珠,欺瞒那丁复。
“大人,”忽地,狱卒自牢狱疾出,步履匆匆,神色张皇,直奔严县尉面前。
“慌什么!县衙重地,岂容失仪!”严县尉眉头一蹙,沉声斥道。
狱卒强自定神,躬身将手中一叠状纸呈上。
最上那份,正是丁复画押具结之供状。
狱卒禀道,“丁复业已供认,八月初二午时,其在瓦肆附近的酒肆宴请青阳妖道,并从青阳手中取得此串人骨念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