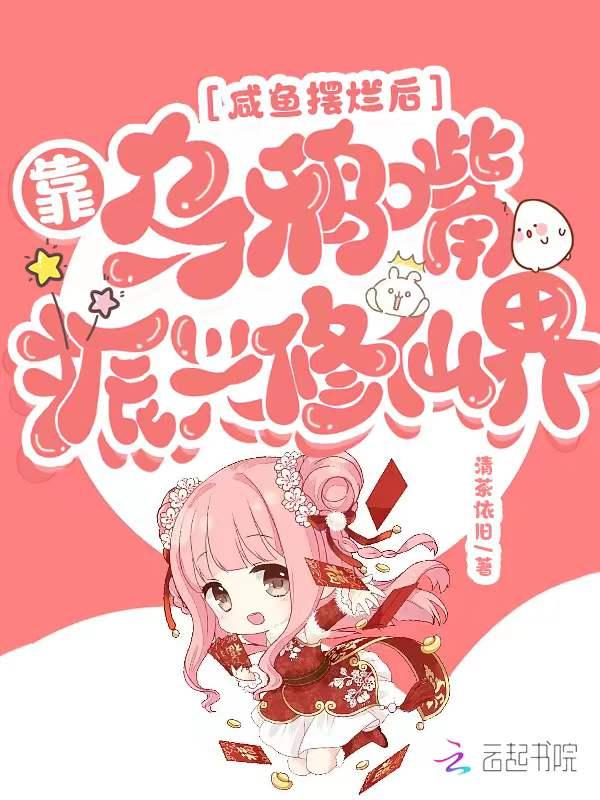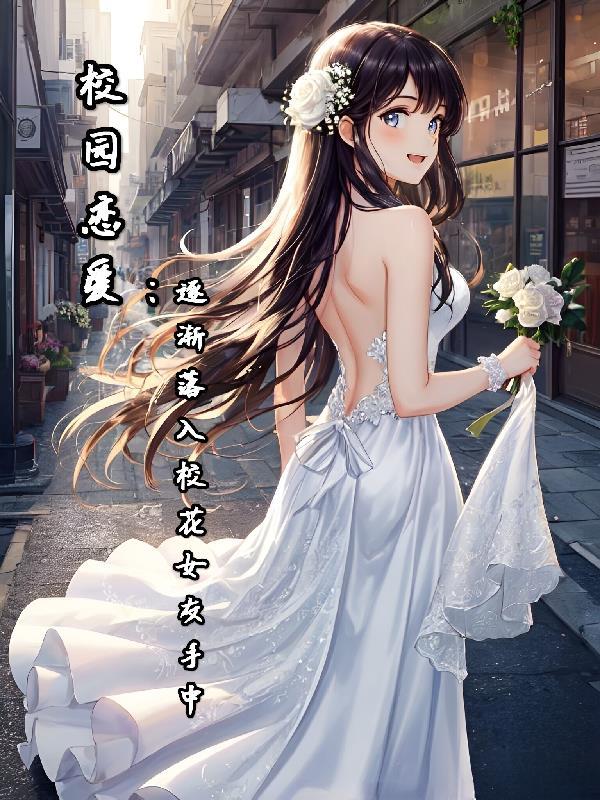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迷魂阵 > 第 5 章(第2页)
第 5 章(第2页)
此地与去往洛阳的路是彻底相反的方向,照理说谢玉生是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裴峻不由发问:“您怎么在这?”
谢玉生瞥了这两个小辈一眼,照理说他们此刻应该呆在御城山中修行,没道理会出现在此地。
“我还没问你们呢,你们怎么在这?”
一阵诡异的静默后,双方几乎异口同声地问起同一个人的下落。
“叔父呢?”
“你们家主可在?”
几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皆是满脸疑问。
裴峻问谢玉生道:“叔父不是和您一道去了洛阳吗?”
谢玉生答道:“原本的确是这样,不过出发前,你叔父好像临时要去见什么人走开了。他同我约好等处理完事情在这所茶寮碰面。原本以为他不会走开多久,可眼见着这都过去一晚上了还没见他过来,我还正奇怪着呢。”
裴峻和裴陵听他这么说,心中疑虑更深。
他们家主这人,恪守信义到了近乎固执到地步。曾听族中长辈说起过,从前家主与同门约定好时辰比剑,中途因救人而迟到了一刻钟,事出有因,大家都体谅他,况且只是迟到了很短一段时辰,并不影响比剑,无人为此责怪于他。
但等比完剑后,他自去领了重罚。在他眼里,放下与他人的约定而以救人为先,是为义。与人比剑需守时,是为信。无论因何理由失信,失信便是失信。
他待人接物一向礼数周全,不是会让人久等的性子。既与谢玉生约好处理完事情就在茶寮碰面,那便说明这件事于他而言并不难处理,他很快便能解决完。
与人约好要碰面,又一晚上没赴约。这种失礼又失信的事情,实不像他平日所为。
这中间必定是出了什么岔子。
裴峻对此倒不怎么担心,毕竟以他叔父的修为,当世也没几个人能奈何得了他,出不了大事。
裴陵性子比裴峻沉稳,心思也比较细,忧虑的事也更多,他总觉此事有些蹊跷,想了想,问谢玉生道:“谢前辈可知家主临时说要去见的人是谁?”
谢玉生转了转手中的翠玉扇子,回道:“那我就不知了。你是清楚的,你们家主公私分明,不爱探听别人私事,也不喜别人多过问他的事。”
裴峻看他这一问三不知的没用模样有点烦,对着他直皱眉头。
谢玉生见他这副一言难尽的表情,不好意思地尬笑两声,道:“要不然你们仔细想想,有没有跟这有关的线索。比如他这阵子有没有特别关注的人,或是特别在意的事?再或者说,这几日他有没有做过一些异乎寻常之事?”
裴峻思索了一番,觉得自己叔父没有什么特别关注的人或事,同平常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叔父对什么都是那副淡漠的态度。
裴陵细细回想后,说道:“家主这几日似乎正留意浔阳那两桩灭门案。”
裴峻斜睨他一眼:“你怎么知道?”
这事连他这个亲侄儿也不曾听说。
裴陵道:“前几日我整理书斋时见家主用剩的纸张上写着浔阳两字,要说最近浔阳有什么值得玄门中人都关注的事,便只有那两桩灭门悬案了。”
谢玉生若有所思应和道:“也是。”
浔阳那两桩灭门案说起来也玄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