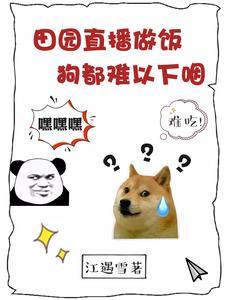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临安杏花饭馆(美食) > 5060(第41页)
5060(第41页)
……
江清澜来到枣子巷,见今日江家少见地中门大开。
一路进去,竟然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唯有春风,吹得院子里的老梅树飒飒作响。
进到二进院子,见一个人在正厅外面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像是在祈祷什么。
不是平林又是谁?
江清澜大惊,他怎么在这里?
平林忙摇了摇头,一张脸苦瓜似的,又抬手指了指里面。
见来人进去了,使命完成,他拔腿就跑,跟身后有鬼在撵似的。
江清澜进到屋里,见玫瑰椅里歪斜倚着个人,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
“怎么是你?”
谢临川道:“怎么不是我?不然你以为是谁?陆斐吗?”
江清澜说不出话来了,他不对劲。
他的周身有浓重的酒气,她甫一闻到,就皱了皱眉。
元宵节潘开的事情,她是真心感谢他的,对他的脸色也好了许多。
那日在杏花饭馆,他们谈到西夏和辽国的事,他的反应也很让她吃惊——
好像他不是这临安城的膏粱子弟,而像原身的父亲江渊一样,也怀着为生民立命的决心。
但他一喝酒——像今天这样,就暴露了本性。
酒壮怂人胆、借酒浇愁愁更愁……酒代表着懦弱、逃避、麻木,她要做一个清醒而理智的人,从来滴酒不沾。
她也不喜欢男人喝酒,此刻,更无法接受他这副颐指气使的样子。
她摇了摇头,淡淡道:“我没有以为是你,也没有以为是陆斐。谁的嗟来之食,我都不想要。”
他这个人阴晴不定的,疯起来,怕是天都要捅。一想到这儿,她只想立刻离得远远的。
便从袖中掏出两张银票,放在面前的长几上。
“这是之前说好的,一千二百两银子,地契、房契和钥匙拿来吧。”
谢临川却没动,垂眼盯着那银票看了半晌:“你的钱从哪里来的?”
“自然我是开饭馆挣的。”
江清澜立刻道,但话一出口,就后悔了。我与他解释什么?便道:
“谢世子,我忙得很,你若是诚心卖房,咱们尽快交接。若不诚心,我就走了。”
谢临川嗤一声:“你那个小破馆子,挣得了这么多?”
他还记得,她在中瓦摆摊儿的时候,得了他五十两银子,高兴得欢天喜地的。
江清澜听他语带讥讽,知他喝多了要发疯,不想与之纠缠,一句话不说,抬脚便走。
手却让人拽住了,往后一搡,靠在墙上,浓重的酒气将她包围:
“你怎么挣的?与薛齐虚与委蛇?与陆斐暗通曲款?”
“不求闻达于诸侯,唯苟全性命于乱世[1]。你的法子,便是这么……不堪?”
江清澜一怔,霎时脸色雪白,一字一句道:“谢临川,你说什么?”
他虽然张扬跋扈,一时要打这个,一时要杀那个,但到底,也没做成个什么。
他以前,也从未对她说过这般折辱的话。
谢临川将她半笼在怀中,因为酗酒,眼尾有些发红:
“你们两个人每天在密谋什么?他凭什么分这么多银子给你?你可知他……”
他到底没把这句话说出来,他不敢赌。
他有些自嘲地一笑,拥着这颗看似温顺、实则倨傲的心,凝视着这张娇柔却倔强的脸,轻轻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