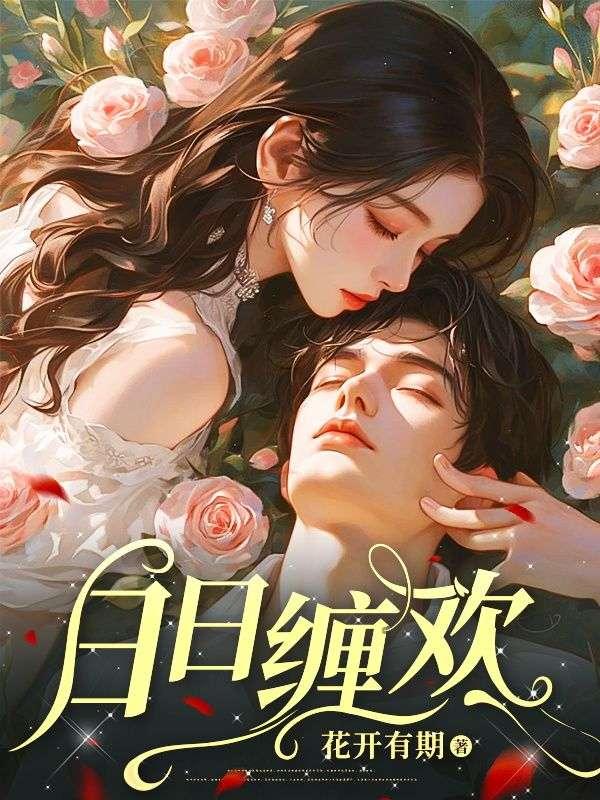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临安杏花饭馆(美食) > 5060(第4页)
5060(第4页)
谢临川脸还沉着,随手一丢,那根巾子落到了陌山头上。
“不去。”
陌山取下巾子,笑嘻嘻道:“那……可要去府署,与刘师傅推演兵法?”
谢临川撩起袍子,旋风般往旁边的水房走。“不去。”
见人快进屋了,陌山一咬牙,把窗户纸捅破:“爷,我听说,春波河上结了冰,站在八字桥上看,怪好看的。爷可要去瞧瞧?”
谢临川脚步停下,撩起眼皮,看他一眼。
结冰,有什么好看的,这小子,脑子被狗啃了?!
然而,八字桥……他心里确实有点儿痒。
可是……
他心里像有猫儿在抓似的,烦躁起来:“哪儿也不去,回王府!”
陌山、平林对视一眼,暗自叫苦不迭。
我的爷哎,你别留在家里祸害人了!你自己跟人吵架,整成了误会。这会子,又拉不下脸去求和。赖着我们什么事儿呢!
这几天,他俩被折腾得够呛。
这位爷不是嫌花红了,就是嫌草绿了,一径地鸡蛋里挑骨头。
连门房上的狗,因为在他经过时叫了一声,差点儿成了锅狗肉汤!
两人苦着脸,你推我、我推你的,谁也不愿去水房近身伺候。
恰此时,一个小孩儿一溜烟儿跑进来,累得气喘吁吁。正是外院儿的跑腿儿青锋。
陌山斥他:“嘘——小声些!爷在里边儿沐浴,扰了他清静,你有几条命来赔?!”
青锋却不怕,掏出个信封,笑嘻嘻道:“两位哥哥,此物正是我们的救命符呀!府署的杨大人说,爷只要一看到这个,保准儿高兴!”
原来谢临川不高兴,不止连累得他们怨声载道,连杨松也是绞尽脑汁、上蹿下跳。
平林、陌山虽有些疑惑,但杨松自来稳妥,他二人就把信封送了进去。
谢临川正在浴池中闭目养神,听闻有信,就撩起眼皮看了一眼。
平林看得真真儿的。嘿,这一眼,真跟钉子似的,瞧见了就挪不开了。
谢临川勾了勾唇角,怀中乱抓的那只猫儿忽的不见了。
他腾的起身,用巾子胡乱一擦,卷起窄袖单衫就走。
“备马,去八字桥上看冰!”
……
早市已过,午市还没到,杏花饭馆里,一个客人也没有。偶有几个人,都是来买了饮子带走的。
正是悠闲的时候,江清澜便挑了个黄澄澄的柚子来剥。
且说这柚子,非得用刀切成花瓣状刀痕后,用手剥不可。
直接削皮,伤了果肉,掰瓣时水淋淋的,既不好看,又显埋汰。
用手剥呢,一则全了果肉,二则柚子香气四溢,许久后尤在指尖留香,颇有些雅趣。
这个柚子有些大,剥去了黄皮后,内里白色的果肉还有一个足球大小。
饶是江清澜在厨房里经常颠锅,把手劲儿练出来了,想要对半掰,一下亦不能成功。
她低着头道:“蕙姐姐,帮我递块巾子……”待雪白巾子到手边,接过擦了擦手,又试了一下,还是掰不开。
“我来帮你吧。”谢临川往前俯着身子,笑眯眯地看着她,很是亲切友好。
如今隆冬,他却一点儿不怕似的,穿一身白地卷草纹圆领窄袖单衫。
周身凛冽的霜寒气,令他面颊冷白、乌发与眼睫却十分浓黑,有一种冬日凛冽的英俊。
他什么时候进来的?江清澜微微蹙眉。
一见他那副笑眯眯的模样,她心中又狐疑:他是失忆了?还是二皮脸病发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