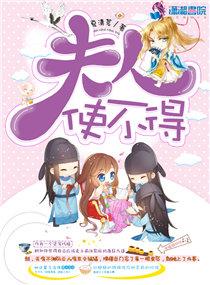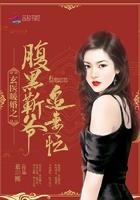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困鸟 > 28姜柔(第4页)
28姜柔(第4页)
可我没别的办法,继续调查他,是唯一能走的路。
多幸运。
我赌赢了,李怀舟的确是杀害陈幼宜的真凶。
连环杀手收藏受害者的遗物,在犯罪心理学上并不罕见,但像他这样大胆,居然把它大摇大摆随身携带的,屈指可数。
想想也是,这款挂坠随处可见,远远不够成为定罪的证据。
那一夜,我坐在桌边,一动不动看了李怀舟很久。
为什么选中了陈幼宜?为什么要杀害那三个女人?囚禁她们的地下室,究竟在哪里?
我发了疯般想要知道真相,然而每一个问题,都没法说出口。
注视着李怀舟,我忽然意识到——
他与陈幼宜的姨父,很相似不是吗?
一个是让她生不如死的恶棍。
一个是彻底夺走她性命的人渣。
我想起陈幼宜哭着对我说过的话:
“有时候,我真恨不得他早些死了。”
……
你憎恨他们,想让他们付出代价,对不对?
陈幼宜去世后,宋成浩嫌晦气,待在赌馆不回家,拒绝所有的采访。
李怀舟不可能认出,他是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家属。
我有了别的想法。
李怀舟这个反社会连环杀手,会是一把很好操纵的刀。
我尝试着,把刀锋对准宋成浩。
要终结暴力,最好的方式,是终结带来暴力的人。
吊桥效应十分奏效,经过那一夜,我与李怀舟的关系进了一步。
他更信任我,准确来说,是更倾向于保护我。
这种“保护”不像大鸟将雏鸟纳入羽翼之下的无私,更趋近于自我满足的占有,如果要做类比,就是把一只孱弱的小鸟关进笼子里,不令它逃脱。
为尽地主之谊,李怀舟带我去他家附近的早餐店吃东西。
在路上,我的计划差一点就泡汤。
原定吃早餐的地方,是一家羊肉馆。我走到门口才发现,李怀舟的邻居竟然也在里面——
那个以为我来租房子、告诉我李怀舟家是凶宅的邻居。
和邻居说话时,我戴了口罩、黑框眼镜和棕色波浪假发,他认出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不过保险起见,我还是假意皱眉,声称闻不了太浓的膻味,让李怀舟换了别家。
在他看来,这只是个不值一提的小插曲。
去往面店后,李怀舟对我说起他父母的案子。
作为交换,我也向他介绍了我的高中生活,和我的姨父——
没错,是“我的姨父”。
我把自己伪装成一个饱经虐待、不敢反抗的受害者,让李怀舟一点点相信,再一步步诱导他步入陷阱。
为了更逼真,比起直白向他倾诉,适当的欲盖弥彰能增加可信度。
在烤红薯摊前,被陌生男人靠近,我惊恐发抖,朝李怀舟的身旁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