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小说网>困鸟 > 27姜柔(第4页)
27姜柔(第4页)
凶手在想什么?
我动用已知的所有心理学理论进行分析。
受害者均为长发瘦削女性,反映出凶手对特定形象的执念,大概率与其过往经历存在关联,或代表凶手心中“脆弱”和“可操控”的符号,便于下手。
单纯追求杀戮快感的话,没必要囚禁这么多天。长达十五天的殴打,表明凶手需要通过对他人的折磨获得心理满足,借由这种支配行为,补偿现实中的无能感。
也就是说,凶手极有可能处于长期的社会挫败之下。
选择偏僻地点作案、有意避开监控,则说明凶手熟悉案发地的地形,曾经多次踩点。
囚禁离不开私密空间,凶手不可能住在人来人往的公寓楼,必然独居。
由此,我做出一部分连环杀手的侧写——
缺乏共情能力,操纵欲强,也许表面正常甚至友善,但极度自我中心。
有被虐待史,借由犯罪,补偿深层的心理创伤。
我想找到他。
我必须找到他。
根据犯罪地理侧写的圆心假设,多数连环杀手会把住所为锚点,在可控制的半径内作案。
结合监控盲区的分布,我利用地图和数学模型,筛选、排除、推演,锁定凶手的潜在活动范围,在白杨街地铁站以北。
然后呢?这片范围面积不小,连警察都对凶手的行踪一筹莫展,我更没办法精准定位。
思来想去,我选择了最笨的方法。
由于案件频发,江城住民的警惕心大涨,凶手要想作案,难度呈指数倍增长,一定会时常外出寻找新的受害者。
我既然确定了他的大概活动范围,不妨直接蹲点。
要穿成与受害者们相似的模样,引他下手吗?
这个策略被很快排除,我独自行动,如果被他突然袭击,得不偿失。
那就用另一套不会引起他兴趣的打扮吧。
头戴鸭舌帽,穿灰黑色运动套装,随身携带防狼喷雾和小刀,用录像记下所有遇到的人。
我开始在夜里游荡,揣摩凶手的行经路线——
主要集中于白杨街周边,同时满足邻近河流、避开主干道监控、有隐蔽运输路径的区域。
这实在不算多么高明的手段,成功率微乎其微,但我只剩下这唯一的方法,必须放手一搏。
日复一日,我等待对方的出现。
从希望到失望,再开启第二天新的希望,周而复始,仿佛没有尽头。
我一遍遍安慰自己,没关系,别着急,就像捕食的蛇,总要在暗处花些时间,才能一口咬破猎物的咽喉。
就这样过去整整十天,十天里,我筛选出所有遇见过两次及以上的人,跟踪确定他们的住址,并以寻找租房为理由,向周围住户询问他们的情况。
其中有醉酒散步的大叔,有深夜遛狗的独居者,也有刚下工的上班族,我通过生活规律、不在场证明和性格特征逐一排查,试图锁定潜在的嫌疑人。
破冰点,是某天晚上,我在街头见到一张熟悉的脸。
瘦削,阴郁,两眼细长。
陈幼宜做过很多家教,结束后,往往要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一瓶水。
有次她做完兼职,一边买水,一边和我打视频电话,谈笑间,忽然没了声音。
等陈幼宜付款离开便利店,才告诉我,之所以噤声,是被店员冷冷看了一眼。
我不解:“他瞪你?觉得太吵了吗?我们声音不大吧?”
“不止今天,以前他也这样看过我,有点吓人。”
陈幼宜说:“没事啦,他又没真的对我做什么。再说,这边的家教快结束,我以后就不去那家便利店了。”
陈幼宜去世后,我调查过一切有可能的嫌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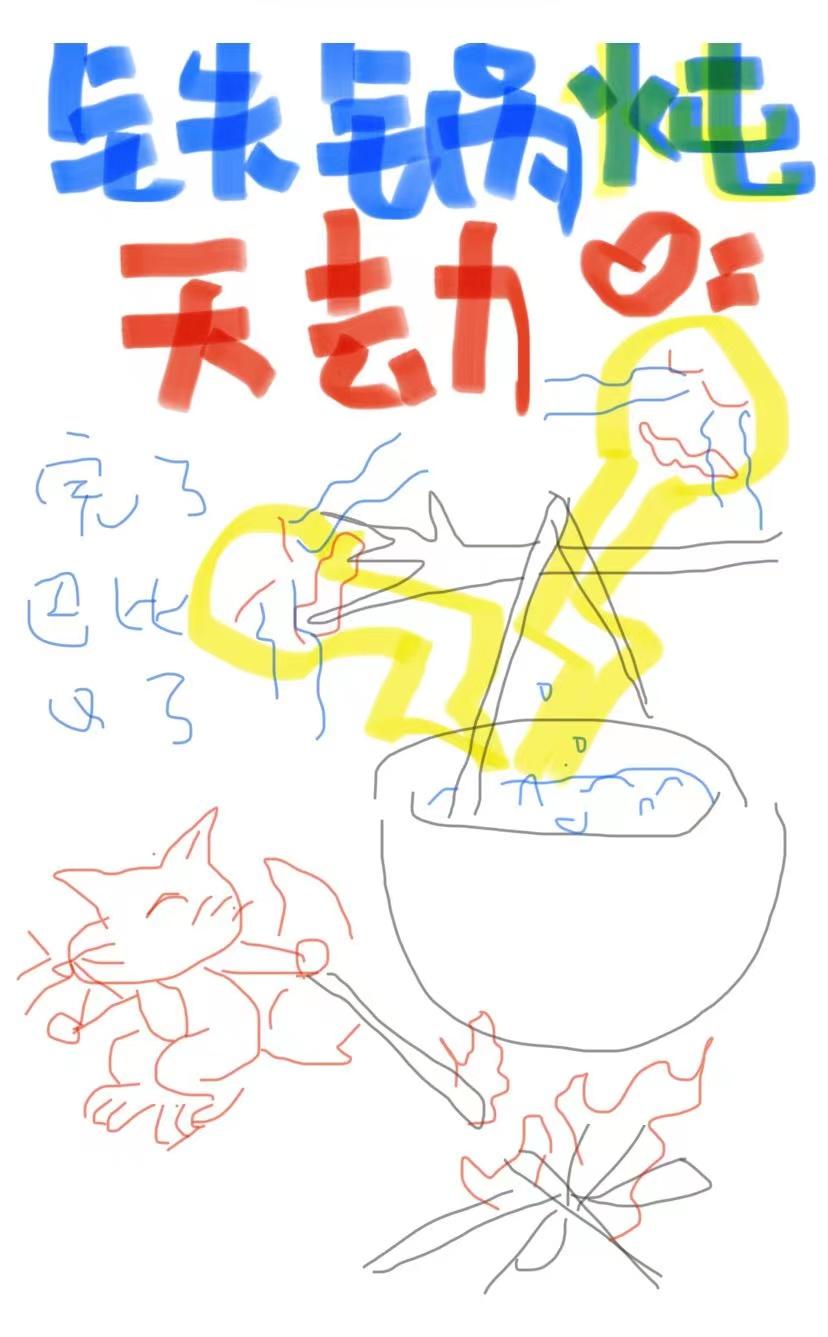

![不好意思,在下冷淡[快穿]](/img/5637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