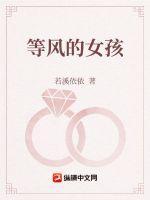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嫁给病弱夫君后 > 3040(第27页)
3040(第27页)
“父亲的心底,难道从来没有过疑虑,没有请外头的大夫来看过吗?”
“宣平郡王府家的二郎君,威远将军的独子,镇西大将军的小儿子,但凡掌了重兵的宗室勋贵家,都有嫡子留在京中,或打理族中庶务,或领个闲职,或就当个富贵闲人。哪怕就是荣国公府,蔺弘方底下都还有嫡亲的幼弟,在崇文馆当皇子们的伴读。”
当年他兄长十二岁便跟父亲去军中历练了。
如果当年落湖后,病根能够去除,身体迅速恢复康健,闻时鸣再过两年,会踏上同一条道路,一条景宣帝并不乐见的道路。
闻时鸣这些年有过猜想,却是林秋白在薛家私邸替他诊脉时的那一席话,拨开了他心头的最后一层迷雾。
闻时鸣看着闻渊越来越难看的神色,语气并无责怪之意,甚至带了宽容的理解,“我不想以恶意猜测陛下或父亲的决定,却也不想以富贵闲人的方式过这一生。”
闻渊说不出话来。
自小儿子体弱养病起,他带时瑄练武从军的光阴更多,每每进入沧澜馆,闻到那种像是倒扣了药碗般的闷苦味,心头就会泛起愧疚,久而久之,却同他疏远了。
小儿子看着不动声色,心头竟已想了这些许多。
当年之事,他确实有过疑虑,也请过信任的军医来看诊。静养是一条道,锻炼是另一条道,闻时鸣当年是那般虚弱,要重新习武乃至于恢复到原来的康健灵活,需要吃的苦头流的汗,不知要几多。
他一点不忍,加上权衡利弊,替他做了选择。
闻渊面色复杂,将小儿子在他眼里显得有些羸弱的身躯,从头到脚看了一遍,闻时鸣实则肩宽腿长,骨架周正,脊梁挺得笔直,是他闻家男儿该有的模样。
他脚步一转,“你跟我走。”
闻时鸣留在原地,并未跟上。
闻渊回头瞪他:“不是要借力吗?不要了?”
这夜,闻时鸣回到沧澜馆,已是亥时一刻。
明月别枝,庭院寂寂,静得听见藏在一丛丛花草里的静静虫鸣。沧澜馆许久没有这样安静过,他推开寝屋的门,没听见脆生生的“夫君夫君”,绿玉席上空落落,还留着她今日起身时乱卷的薄被,看得出走得匆忙,绮月或云露都没来得及整理。
闻时鸣在绿玉席坐了一会儿,到底觉得凉。
他拎起程月圆用的枕头,丢到了自己的紫檀床上,却见他的药枕上放了张皱巴巴的小纸,打开来,小娘子歪歪扭扭蚯蚓爬一样的字迹:
“夫君,我走啦。”
“做假铸币的坏蛋,要早点抓到啊。”
他失笑,将纸张抚平,郑重地压到了药枕底下。